论坛回顾|《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与新东北文学》
从《平原上的摩西》开始,作家双雪涛用想象力建造了历史寓言色彩的“北国幻境”,成为文坛最受关注的青年作家之一,先后斩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单向街书店第三届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第三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等诸多荣誉。双雪涛作品英文译本精选集《艳粉街:三个中篇》(Rouge Street)已于4月19日面世。
《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与新东北文学》中英双语论坛由哈佛大学、罗格斯大学、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蒋经国基金会共同举办。与会嘉宾们探讨了《艳粉街:三个中篇》(Rouge Street)精选的三部作品:《飞行家》、《光明堂》、《平原上的摩西》,并扩展到双雪涛的文学世界、新东北文学、国际合作等议题,以及译本对英语文学世界的意义。来自全球的直播观众近千,共同展开了深入的提问讨论。
本文为此次论坛的文字整理,与各位文友分享。
《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与新东北文学》中英双语论坛由哈佛大学、罗格斯大学、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蒋经国基金会共同举办。与会嘉宾们探讨了《艳粉街:三个中篇》(Rouge Street)精选的三部作品:《飞行家》、《光明堂》、《平原上的摩西》,并扩展到双雪涛的文学世界、新东北文学、国际合作等议题,以及译本对英语文学世界的意义。来自全球的直播观众近千,共同展开了深入的提问讨论。
本文为此次论坛的文字整理,与各位文友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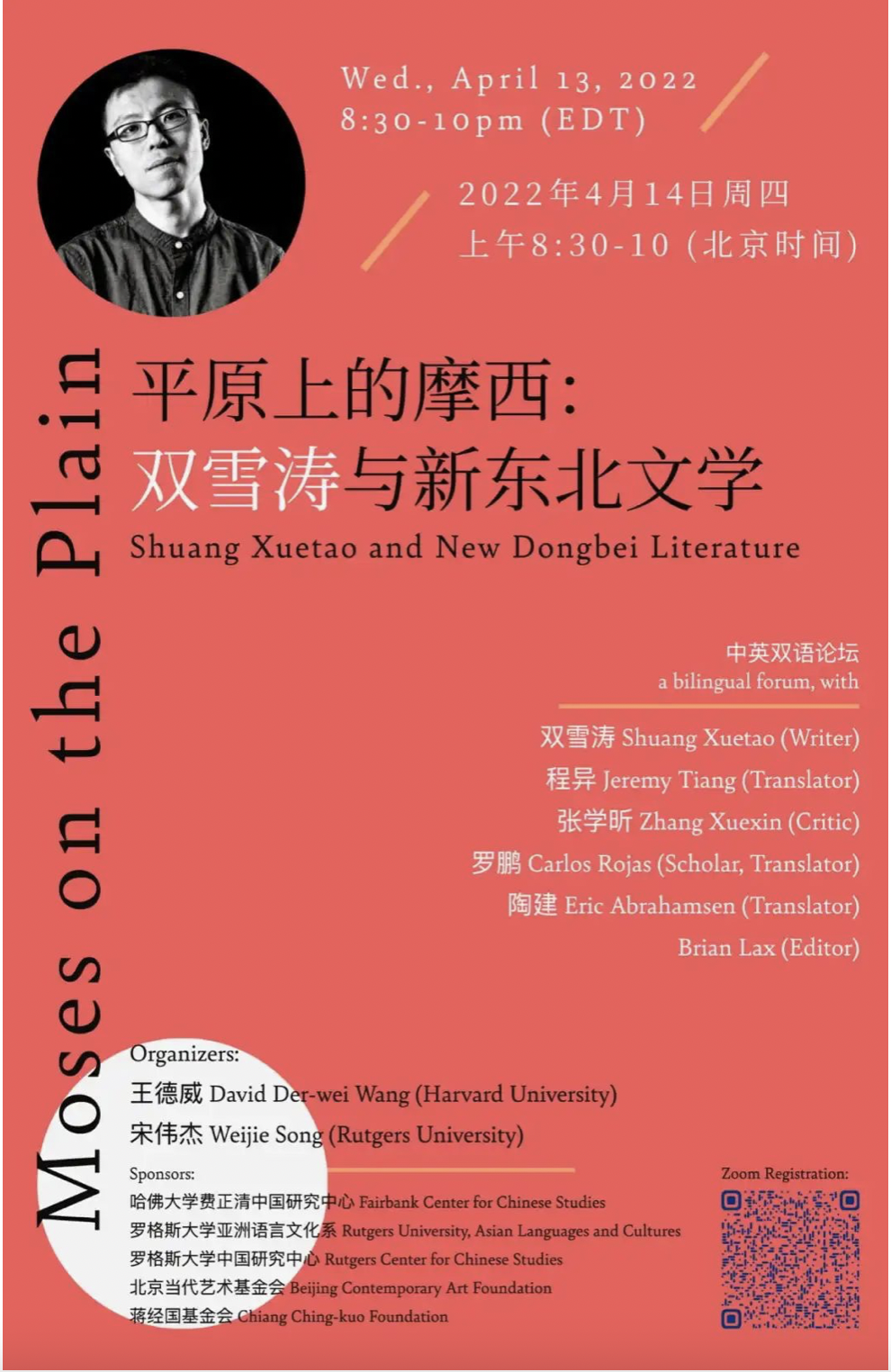
关于对谈嘉宾
关于作家

双雪涛
Xuetao Shuang
1983年生,沈阳人,小说家。出版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猎人》,长篇小说《聋哑时代》《天吾手记》《翅鬼》,曾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奖,2020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刺杀小说家》已被改编成电影。
关于与会嘉宾
学术主持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暨比较文学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大陆长江学者,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著有《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二十家》,《如此繁华》,《后遗民写作》,《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现代“抒情传统”四论》,《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新加坡经验》,《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Fictional Realism in 20th 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y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述》,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 Why Fiction Mat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等。主编Harvard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

宋伟杰
Weijie Song
罗格斯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副教授,荣获校董会优秀研究奖、优秀教学校长奖。著有Mapping Modern Beijing: Space, Emotion, Literary Topography (《测绘现代北京:空间,情感,文学地形图》)、《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合编期刊专题《东北研究》、《环境人文、生态批评、自然书写》等。译有《被压抑的现代性》,合译有《跨语际实践》、《比较诗学》、《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解大众文化》、《大分裂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等。
嘉宾

程异
Jeremy Tiang
2022年普林斯顿大学驻校翻译家,2022年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2018年凭英文长篇小说State of Emergency曾获新加坡文学奖。同时,他积极投入文学翻译,译过二十多本中文著作,包括张悦然、英培安、顔歌、陈浩基、骆以军、严歌苓、刘心武和苏伟贞的作品。程异也创作並翻译戏剧作品。

张学昕
Zhang Xuexin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心主任。曾发表文学研究、评论文章300余篇,出版专著《真实的分析》、《唯美的叙述》、《话语生活中的真相》、《南方想象的诗学》、《穿越叙述的窄门》、《小说的魔术师》、《苏童论》、《阿来论》、《细部修辞的力量》。主编有“学院批评文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百年百部短篇小说正典》。2008年,获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

罗鹏
Carlos Rojas
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系教授,曾任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妇女研究中心、以及移动影像艺术研究中心副教授,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学与艺术的研究。著有《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长城:一种文化史》以及《离乡病:当代中国的文化、疾病、与国家改革》。曾与王德威合编《书写台湾:新台湾文学史》,与周成荫合编《反思中国大众文化:经典的经典化》和《牛津中国电影手册》;与白安卓合编《牛津当代中国文学手册》等。此外,他也是当代多本重要华文文学经典,如余华的《兄弟》 (与周成荫合译)、贾平凹的《带灯》、黄锦树之短篇小说集、以及阎连科的《四书》、《受活》、《炸裂志》、《日熄》、《我与父辈》、《坚硬如水》等作品的英文译者。

陶建
Eric Abrahamsen
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网站《纸托邦》(Paper Republic)创办者,2006年起从事中国文学翻译,译过苏童、毕飞宇、阿乙、盛可以、徐则臣等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王小波的杂文著作获得2009年美国PEN笔会颁发的文学翻译奖,2015年他获得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

Brian Lax
美国大都会出版社 (Metropolitan Books) 助理编辑,主要发掘小说、回忆录以及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非虚构小说。双雪涛的《艳粉街:三个中篇》(Rouge Street)是他参与编辑的第一本书。在进入出版业之前,他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在中国上海及周边地区教授文学和散文。
论坛精彩内容文字回顾
王德威:
大家好,欢迎,无论你们身在何处。我是王德威,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我和罗格斯大学的宋伟杰教授一起主持这次线上论坛,向大家表达最热烈的欢迎。我们很高兴有幸邀请到特别嘉宾双雪涛先生和《艳粉街》的译者程异(Jeremy Tiang)先生。
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四位学者、译者和编辑加盟,他们是辽宁师范大学的张学昕教授,杜克大学的罗鹏(Carlos Rojas)教授,还有来自西雅图的陶建(Eric Abrahamsen)先生,他是纸托邦(Paper Republic)的总监,《路灯》(Pathlight)杂志的翻译和编辑;最后,英文版《艳粉街》的编辑Brian Lax先生,他在推动《艳粉街》的出版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艳粉街》是一个作品集,收录了双雪涛先生最好的三篇小说,我们今天的谈话也将由此而始。
《艳粉街:三个中篇》(Rouge Street)书籍封面,图片来源:哈佛大学
双雪涛先生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有前途的作家之一,不管是在中国大陆,还是放眼海外。他的作品在电影行业也颇负盛名,已有三部电影根据他的作品改编而成。尤其重要的,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双雪涛还是一种文化的代表,是“东北文艺复兴”现象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但是今天可能着重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讨论东北文学和双雪涛,以及同时书写东北的其他重要作家。我相信双雪涛不是唯一记录家乡东北的人。我知道今天在线的班宇,还有郑执,以及许多其他年轻的、崭露头角的作家,他们都在倾力书写这个幅员辽阔的东北地区。
所以我认为今天的论坛将是中国当代文学以及翻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一次深入的探讨。首先我想请嘉宾们共同对话,也向双雪涛和程异提问,请宋伟杰教授来主持这一部分。
在中场的时间,我们将邀请双雪涛和程异各自朗读中文作品及英译本的一些精彩的片段。在论坛最后,希望还能有时间进行观众问答。
对我来说,我第一次知道双雪涛这个名字是一个学生的推荐。
2015年,一个学生来找我,对我说:“王老师,你读过双雪涛吗?”我问,谁是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这个奇异的标题下究竟讲的是什么?当然,我在阅读这篇小说和其他作品时获得了愉快的阅读体验,我非常喜欢这些作品。最终,我帮助《平原上的摩西》在台湾和海外华人社区出版了繁体字版。所以从2017年开始,在我心中,双雪涛绝对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佳水准之一。
宋伟杰:
非常感谢王老师。非常荣幸能共同主持这个双语论坛,欢迎我们的嘉宾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观众。请允许我对今天的嘉宾再补充几句,希望能更好地介绍他们的成就。
雪涛,人们已将他与村上春树和海明威相提并论。程异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驻校翻译家和布克国际文学奖的评委。学昕来自东北的大连,文学批评的领军人物。罗鹏,我们的老朋友、老同学,他不仅是高产的学者、编者,也是备受好评的译者,翻译过余华、贾平凹、黄锦树、阎连科等人的作品。纸托邦网站的创始人陶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察者,翻译过王小波和徐则臣的作品。Brian,普林斯顿毕业,曾在上海教书,这也是他作为编辑出版的第一本书。还有支持合作此次活动的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的理事长崔峤。我们有很多问题准备提问。
首先请罗鹏教授代表我们大家提问。
01
中、短篇小说:文类与突围
罗鹏:
第一个问题是谁选择了《艳粉街》里面这三部作品,作者、译者还是编辑?谁定的英文版小说集的书名(标题跟里面中篇小说的名字不一样)?还有,Brian,正如伟杰提到的,我也从网上资料注意到,这是你担任编辑洽购出版的第一本作品。你是怎样选择了双雪涛,尤其是他的作品从未被英译过?对于第一次出书的编辑这似乎要冒不小的风险。
Brian:
谢谢你的问题。伟杰提到我来纽约从事图书出版之前曾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我曾在普林斯顿学习文学,现在是一名编辑。大都会图书(Metropolitan Books)有出版小说和译本的历史,我们刊行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等人的作品,我们的出版业务也一直跟中国有关。与中国的关联,始于中国政府邀请我们去介绍美国的出版业,于是试着关注中国作品。
初识双雪涛是在非常了不起的网络文学杂志《渐近线》(Asymptote)上看到了译成英文的短篇小说《白鸟》 ,就连这个标题也让我觉得很怪。
《白鸟》被译成英文的短篇小说于《渐近线》(Asymptote)出版,图片来源:asymptotejournal.com
它由七个不相关的段落组成,它们全然不同,但又从整体上彼此关联。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的世界,非常隐晦、神秘,让你不禁要深深地关心这个作家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尤其是他的写作全是关乎生死。
它直接触动了我作为读者的敏感神经。程异在Brick杂志上翻译的另一个故事(《跷跷板》,Teeter-Totter)也是非常神秘,甚至令人毛骨悚然。我的兴趣达到了顶峰,于是就去找了上海的群岛图书,双雪涛的版权代理,现在群岛图书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成立了上海译文的国际版权中心。
罗切斯特大学做过一个著名的研究,是关于翻译作品在美国出版的数量。我记得是占到3%左右,再具体到虚构作品,只占将近0.7%,这当中又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中文作品的译本。所以我有一种使命感,要把这种独特的、吸引人的作品带给英语读者。
编辑出版这本书很美好,我也感到非常骄傲,它已经在美国引起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把《艳粉街》列入了4月的12本月度新书推荐。我非常欣赏双雪涛的想象力。
宋伟杰:
现在有请双雪涛和程异。
Brian先看的是《白鸟》,七个短篇里面有不同的文体,其实隐含着你写作的密码,2017年发表于《收获》。Brian是从《白鸟》进入到你的(作品)翻译。所以我们非常想听听雪涛和程异为什么选这三部中篇,其中各有一个超越的向度,以及英文的翻译是怎么进行的。

《白鸟》,图片来源:asymptotejournal.com
双雪涛:
首先谢谢大家,看到这么多朋友一起来讨论这本书就特别感动。
其实我也在努力回忆三篇小说是怎么成集的。当时要做一本英文小说集的时候,我和彭伦(群岛图书)还有程异、Stephen Edwards (群岛图书)在讨论,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在头脑里想象,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本挺均匀的书,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准不准确。比如在大陆常见的小说集,其实通常可以看成是作者在某一段时间写的小说的合集,但是这种小说集的整体性一般来说都不是很强,它更像是一种小说的搜罗。
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包括后来自己做的小说集,我想把它做成一种有一点建筑感的作品,它的各个部分是有关联的,但这种关联又不像是完整自洽的长篇小说那么紧密。恰巧我就想到了这三篇。这三篇小说首先体量差不多,比较均匀,不是有长有短,在阅读的过程中是从一个地标到另一个地标的感觉,这三段路长度是差不多的。
另外这三个小说其实都是我写得比较顺利的小说。我经常回忆自己写小说的过程,这三个小说写得都不算是特别费劲,可能《光明堂》的第三个部分费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整体来说这三篇小说写得还是比较顺的。
首先在故事上算是比较通顺的。刚才伟杰老师也讲了,这三个小说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种超越的向度。比如像《飞行家》,它其实没有像《光明堂》那么强的宗教心境,但是在我心里它也是有“超越性”的一个东西,但它具体是什么我也很难解释清楚。

《刺杀小说家》根据双雪涛短篇小说集《飞行家》中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图片来源:豆瓣
所以这三个小说在我心里有一种非常隐秘的关联,这个关联我相信程异还有Brian,他们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都有所感受。
程异:
回想当初,我感觉更像是我们一起做出的决定——选择这三部中篇小说以及用艳粉街这个书名出版。
一部分是由彭伦首先向Stephen 和 Brian提出的。正如雪涛提到的,这三篇小说非常平均,他们彼此自洽且融合。
尽管只有几个小角色重复出现,但展现出这三篇小说的内容共享同一个宇宙/世界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神秘而难以言喻的东西。它们是内在关联的,尽管它们都是独立的叙述。我们认为通过这本合集,是向英语读者介绍双雪涛的最好方式。
我们一度考虑用其中一部中篇小说再加上一些短篇作品。但实际上,我认为三部中篇故事是更好的选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短篇小说不能给到的满足感。这就有了现在的作品。我真的很期待看到读者的反应,因为中篇小说在英语世界是相当被忽视的体裁,但在中文世界却非常普遍。所以我认为把这些作品呈现给英语读者,也是表达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宋伟杰:
其实程异的中文也非常好,我听过他的演讲,他有些问题已经和雪涛构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呼应。
张学昕教授,出生在东北,黑、吉、辽三省全部走遍,现在在大连。短篇小说在当代可能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文类,可是回到鲁迅时代,短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类。学昕对短篇小说的研究也一直有持久的关注。
下面有请张学昕教授,谈一下雪涛的短篇、中篇或者长篇。然后再请陶建进一步来表达他的看法和观察。
张学昕:
刚才两位谈到为什么选《光明堂》、《飞行家》,还有《平原上的摩西》。雪涛的大部分作品我都看过,我个人的想法,《光明堂》,《平原上的摩西》,包括《飞行家》,它们有更多哲学和宗教上的考虑,在信仰层面、从题材上来讲都是带有一种宗教的意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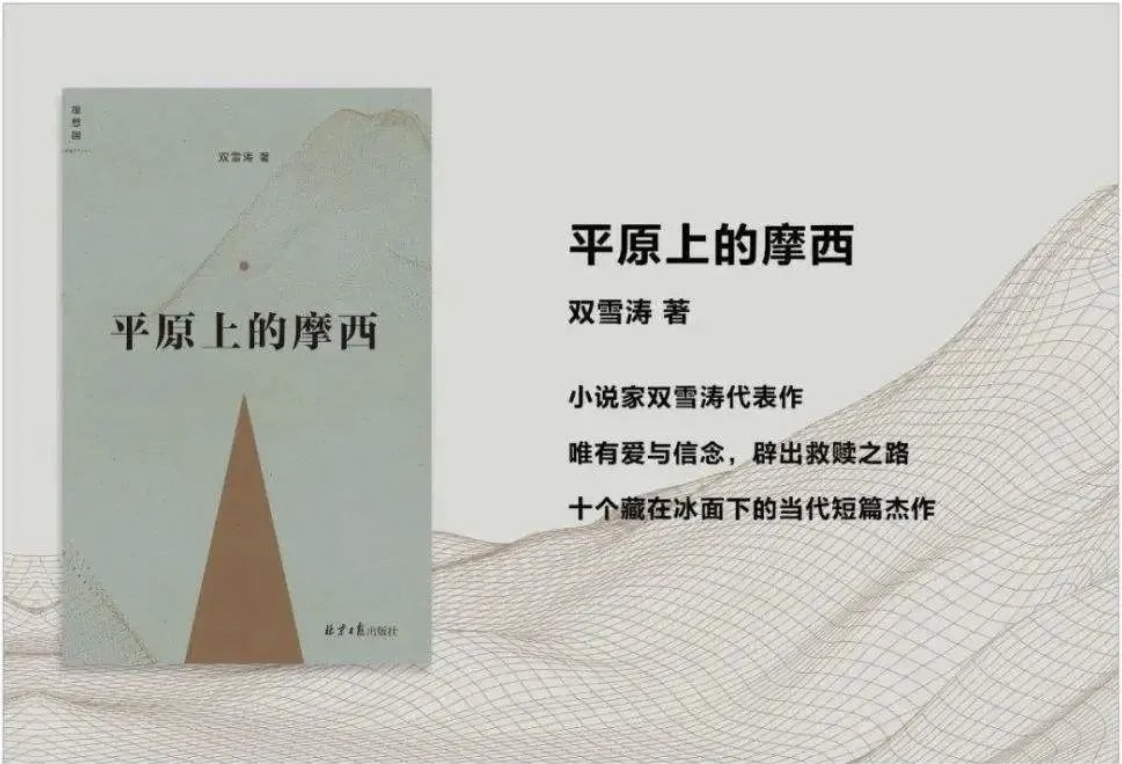
双雪涛作品《平原上的摩西》,图片来源:豆瓣
在叙事层面,欧美在文体上没有中、短篇之说,中篇和短篇之间的临界点是很微妙的,所以我们也不妨把它作为短篇来看,肯定比小一点的短篇更充分。我注意到结构上,像《光明堂》和《飞行家》,都是作为我们子一代对父一代的一种呼应,就如我们说雪涛、班宇这一代作家他们是来打捞父辈记忆的,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当代小说近10年创作的一个空白。
我们关注的是他们这一代——80后写什么。像当年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即在40后作家、50后作家把各种题材都写尽的情况下,苏童、余华、格非也面临着如何突围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很多题材也都被70后、60后写尽的时候,雪涛、班宇、郑执这一代作家,他们要打捞历史,他们要反抗遗忘,保存共和国在东北的这一段沉痛记忆和人性的哀伤,并在这种哀伤、失败中来重建一种尊严。
从叙事层面,《光明堂》和《飞行家》不断地闪回,两代人的不断对话,是一种交叉。《平原上的摩西》让我想起《交叉小径的花园》这么一种结构,众声喧哗,由人物来牵头,不断交叉,有讲述的,有被讲述的,或者都是讲述的,也都是被讲述的。
从文体层面,我觉得选这三个中篇也非常符合雪涛创作的一个整体特点,他的创作和班宇以及郑执的创作有一定的同质性,但是每个作家也有各自的异质性,选这三个中篇或者短篇能体现雪涛自己的文体特点,包括题材选择上他的倾向。我是这么理解选本的。
02
子一代与父辈:乡愁,巨变,尊严,考验
双雪涛:
感谢张学昕老师。我的英语不太好,这是我少有的听懂的部分(笑)。
伟杰老师也把Brian写的那封信拍照后通过邮件发给了我,我看了还是很感动的,因为《白鸟》那篇小说我自己是很喜欢的,没有想到因为这么一个小说产生了奇妙的缘分。
从《白鸟》聊起,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小说当然和《平原上的摩西》、《光明堂》、《飞行家》都非常不一样,但它是我写得比较自由自在的、内心非常喜欢的一个小说,所以我觉得它在某一方面跟我们这次选的三篇小说也有某一种关联。其实我对父辈历史,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想得很清楚,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身边的人,我是从人出发去思考一个小说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从来没有说一定要去为父辈做点什么,但是恰巧我们这代的孩子跟我们父辈的关系比较特殊。我是个工人的儿子,我的父母其实都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失去了工作,其他的父母也失去了工作,可能大家都在某一个时期,突然间父辈的尊严受到了考验。而且我觉得在某一种层面上,他们失去的是一种“乡愁”,这种“乡愁”只能在工厂里获得。工厂“粉碎”了之后,他们不但失去了一个工作,也失去了自己的社团,失去了自己所依附的某种信念。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事情。而且据我的回忆,我觉得这种东西严重打击了他们的自信。

艳粉街工人村里的老人,图片来源:网络
一个父辈的自信是很重要的,即使自信是虚无缥缈的,也很重要。
但是在那种时期很多失去工作或下岗的父辈自信心都受到了某种影响,因为他们的工作只能在工厂里做,一旦脱离工厂可能他们的价值就非常的低,非常的小。
这也严重影响了我们这代孩子的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之后的文学道路,也是你人生的选择,你会感觉到某一种不安全感,你会感觉到甚至对父母这一辈的某一种叛逃——他们的那个道路,经过事实证明是有问题的,你会觉得我要去走另一条路。
当长大了之后,再去写这段东西,其实是感觉通过文字得到了一个机会去重新理解这个东西。而且现在我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理解这个故事。我觉得我可能还会花时间再去做这个工作。
陶建:
目前还没有人给在座的、可能还没有读过这些书的人介绍一下故事背景,所以我简单概括一下:这些故事主要发生在90年代的中国东北,尽管它们可以追溯到文革,也可以推进到现在的沈阳,一个曾经非常繁荣的地区不再繁荣,整个中国的经济都在变化,东北的经济也在变化。中国东北的社会结构垮了,工厂停产、人们失去工作。
这本小说非常有力量,这是由历史决定。很多中国小说都是如此。我不想抱怨中国当代小说,但我们从当代中国读到的很多小说都是对中国过去困难时期的历史探索,你常常会觉得结局早已注定,就像我们都知道文革是怎么结束的。
我们都知道90年代那些事,人物就像作者的傀儡或棋盘上的棋子。我们读到他们坠向低谷,因为历史和社会那些巨大的力量,他们与无可逃避的宿命遭逢。这往往读起来很累人,因为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结局,你觉得就是在看一条历史的弧线。
雪涛的小说就绝不是这样。虽然历史对它的影响依旧很大,每一两段都会写到社会历史变革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些强硬地决定了人物命运的环境,但这些人物没有察觉。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种奇妙的开放性。这些人身边发生了的事情糟透了,你也会猜到他们的结局,但他们仍然在打拼。雪涛给了他们足够的行动力、特征和个性,每个人物都完全不同。每个人对未来都各有主意,有自己的奇思异想,有自己的挣扎。他们朝不同的方向努力。

电影《刺杀小说家》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当你阅读时,从叙事本身来看,阅读体验是开放和轻松的。你看着这些人带着各自的奇怪想法和行事原则出现,各种非常复杂的人物渐次展开,你会猜到有很糟糕的事情要发生,但它并不像其他中国小说那样,让你感到沉重,感到可怕。你等着看他们对发生之事作何反应,实际上有种轻松的感觉。这是种美妙的阅读体验。我想这就像是发现了一种书写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新方法。
我认为这种方法对中国的作家和读者来说是很健康的,而且它也更有可能吸引海外的读者。这些读者带着好奇心来读这本书,他们不希望被这种可怕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重压所累。这本书对他们来说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那些精彩奇特的人物和数量惊人的暴力。
向Brian和程异提问:你们是否想过这本小说将如何面对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固有看法?你们认为这本书会顺应,还是颠覆某种成见?你们会把它归到某个现有的文学类别吗?
我在东北长春呆了不少时间,书中的暴力并不会让我惊讶。但我能想到:会有很多不熟悉中国社会的英语读者,会觉得这个地方很粗暴,到处都是流氓,人们动不动就要回家“抄刀子”。我在想从出版或者翻译角度来看,这是否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程异:
谢谢陶建。我其实不同意你说的,故事的人物结局很糟糕。我觉得你提到的开放性是他们全心信奉的,虽然他们可能各有目标,但只要顺风顺水他们就很快乐。部分原因是他们生存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段,抓到任何东西都是救命的。
所以有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好像什么都可能发生。雪涛用他的神秘元素抓住了这一点,特别是有时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无法真正理解。生存,整体而言是一个谜。我们能做的只是一步步地往前挪。所以没有什么结局是坏,或者说根本没有结局,只是一步步地走下去。说到读者的成见,对一本中国小说的期待,老实说我尽量不去想,因为不是迎合就是拒斥。我的兴趣并不在此。
我认为雪涛的作品也不符合任何特定的类型。总之,我按它本身的样子去理解,按它本身的样子的来翻译,不参照其他。我想这也会让读者按它本来的样子去读这个作品。如果他们有任何特定的期待,我认为很快就会被推翻。因为雪涛写作的一大特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翻到下一页时会发生什么。所以不管读者打开书前带着什么预期,他们都可能会抛开它,重新开始。
03
重访艳粉街:三个超越的向度

艳粉街的棚户区,图片来源:网络
宋伟杰:
王德威老师今年在哈佛开的一门课是“边地文学”,有15位学生和15位访问学者参加,正好这周刚刚讲过雪涛的小说,有很多精彩的发现和讨论,请王老师讲一讲。
王德威:
我想我们在线上的很多读者或来宾,也许对雪涛的作品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艳粉街。当然这可能是你个人经验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你虚构出来的。呼应刚才程异的讲法,经过艳粉街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和人物的交接,最后这个小说产生了很多奇异的、让我们事前不能够料想到的曲折。能不能先请雪涛谈一下艳粉街的来龙去脉?在中国现实主义传统里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为什么艳粉街这么特别?
双雪涛:
谢谢王老师。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艳粉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它在我小时候其实就是一大片棚户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它的房租很便宜,住宿条件非常差,但是面积很大,所以有少量的城市游民——城市的无业者或城市里一些脱序的人,他们就会到艳粉街这个地方,我们也叫艳粉屯——这个词就更偏乡村一点——重新去开始自己的生活。也有一些从乡村准备进城务工的人,他们会以艳粉街作为一个过渡,因为确实这个地方所有东西都比较廉价。

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第二部分:艳粉街》,图片来源:网络
所以它就从一个很小规模的、散落的城乡混合居住区变得越来越大,后来应该是有几千户的人家。这也是我自己在打捞自己的回忆,但是可能因为在一个少年的眼里什么东西都很大,艳粉街是不是这么大,我也确定不了。
它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但并不是很美妙的地方,因为它确实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所以我小时候住在艳粉街,其实不太好意思跟人讲,因为我很多同学都住在一个可能更好的地方。虽然艳粉街的名字看起来很光明,有艳丽、有粉红,但是它其实不是一个明媚的地方。

艳粉街的棚户区,图片来源:网络
等我长大去写作的时候,我觉得写作有一种逻辑,这个逻辑可能会 让你亲近某一种素材,艳粉街就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其实我好像没有几篇小说是正面地、完整地去描述这个地方。《光明堂》是比较充分地写了艳粉街的一篇,其他的几篇可能偶尔提到,或者有一个人要去那个地方,或有人从那边出来,或有些人要去抓人。它更像是个地标,(作为一个地标)也许一个街的名字会更容易让大家记住。
但是我后来也回想自己的小说里,每次写艳粉街的方位都不太对,东西南北可能完全根据心情来,在我内心,它可能也不是完全现实的地方。就像刚才我说到为什么很开心Brian提到《白鸟》,他从这篇小说认识我。我并不一直觉得现实是我一定要去尊重的东西,艳粉街也是这么一个地方。每到艳粉街我都得到一种自由,我不想因为自己回忆里的一些羁绊而损失掉这个自由,所以艳粉街可能在小说里还是以虚构为多,它是我努力构造的,一个能够装载我的一些人物的地方。
宋伟杰:
关于艳粉街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艳粉街在城乡之间,它是个圈层结构,你在《光明堂》里写得很细,有差不多200户人家,有一个复杂的社区和邻里关系。
通过林牧师的描述,从清代到当代,艳粉街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空间,是不是可以想到莫言?是不是可以想到福克纳?艳粉街既是军营,也是居家的场所,可以是土匪窝,也是龙脉的尾巴,是一个宝藏,在当代又是一个可以开采煤矿的产地,对于我来说更像是个棚户区。最有名的棚户区可能就是老舍的《龙须沟》,(梁晓声的)《人世间》里面的“光字片”也是另外一个棚户区的重要文学原型。
所以我就想,如果雪涛现在重访艳粉街,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你怎么样再描述?是一个可以具体锚定的场所,还是一个通过你的情感记忆放大、缩小、扭曲的空间?一个街角社会的故事?

《铁西区第二部分:艳粉街》截图,图片来源:网络
另外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超越的问题。其实我在想三部中篇选得非常好,这里面有三个可能的超越的向度。第一个可能是向上的,《飞行家》李明奇的话,他要飞,飞到哪儿我们并不清楚,骨头很轻的他有向屋顶天空飞行的可能。到《光明堂》可能有一个向下的,比如脏的湖里的鱼,有到社会底层甚至一个想象的地下室空间这样一个向下超越的可能。第三个是平行的维度,《艳粉街》三个故事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走到光明堂,走到沈阳的北陵公园,走到《平原上的摩西》中可以放烟火的人工湖,平面意义上既是平原也是荒原,那种处境是个非常重要的空间设置。

沈阳市北陵公园,《平原上的摩西》故事发生地,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王老师的一篇文章讲到《平原上的摩西》是艳粉街启示录,他说到“信”以及“报信者”要传递的信息是逃脱困境、前来报信。但戴锦华老师也会说到,一定要注意另外一种困境,即逃脱中的落网——你逃掉了,还有另外一个天罗地网在等你。
所以我在想艳粉街的空间设置,它有向上、向下、平行的这样一种超越的、救赎的、甚至救赎的不可能这样一个维度,包括最后《平原上的摩西》杀还是不杀,开枪还是不开枪。这种停顿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悬而未决的信息,一个期待、一个希望还是一个希望的不可能呢?
《平原上的火焰》的剧照,改编自《平原上的摩西》,图片来源:豆瓣
双雪涛:
刚刚您讲向上的、向下的、平面的超越,我觉得对我启发挺大,这几个方向还真的是这三个小说里面包含的。您刚才说的艳粉街历史是我自己编的,我在《光明堂》里写到那段时,我需要一个关于艳粉街的来龙去脉,它是我制造出来的一个关于艳粉街的历史。
它真正的历史好像确实是给皇帝种过胭脂,所以叫艳粉街。我们沈阳本地人叫“淹粉街”,淹没的淹,我有很多年不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后来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查了一下原来是艳丽的“艳”。所以其实在我心里它从来不是一个明确的地标,刚才您讲的艳粉街的圈层格局也是我编的,到底是什么格局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对艳粉街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这个印象我在《光明堂》里写了一部分。我记得有一个盛夏,艳粉街的入口有一棵巨大的树,很多人在树底下下棋、打扑克,这是我们东北人夏天经常在户外干的事,它也是一种社交。我看到一个大概十八九岁的男孩,他在那做一个雕塑,他穿了一个特别洁白的衬衫,旁边都是那些在打牌、在呼喊着玩耍的中年人。这个场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从来不知道艳粉街还有人搞雕塑,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汗流浃背地在一棵树下,专注地做他的作品。我觉得这不但是一种画面,同时也是一种启迪。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艳粉街的孩子,也许有一天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谢谢。

电影《钢的琴》剧照,图片来源:网络
——【嘉宾中英文朗读部分】——
《光明堂》结尾(节选)
朗读者:双雪涛
双雪涛,图片来源:网络
双雪涛:
姑鸟儿说,他流血了吗?我说,没看清,也许是游走了,也许已经把怪鱼拖了上来晾干了,那小子挺有劲儿。她说,他好像托付我点事情。我说,嗯,答应人家就别忘了。
姑鸟儿说,那个泥人我放在阁楼里,我有点想起来了,那个泥人在哪?我说,在光明堂,没有带出来。
她说,那个泥人挺好的,有机会应该去拿回来,还能找到吗?我说,咋不能?一定在某个地方,不会消失的。
姑鸟儿哭了,我第一次见她哭,她搂着我的胳膊大声哭起来,眼泪把我的袖子弄湿了。
她说,光明堂倒了,我妈其实挺迷糊,你说她能找回来吗?我说,肯定能,走出去难,回来容易。
她说,大个儿他妈就没找回来,就丢了。我说,三姑不一样,三姑很机灵,心里有数着。
她说,她在外面没有食堂,吃啥?我说,满世界都是馆子,比食堂好吃多了。
她说,她能忘了我不?我说,哪能?她兜里揣着《圣经》,念一遍就想起你一回。
姑鸟儿把眼泪擦了擦,渐渐不哭了,太阳高悬着,照着树枝上洁白的雪,那雪只和阳光和风接近,看上去十分安宁
姑鸟儿说,你听见我肚子叫了吗?我说,到家给你下碗面条。她说,你还会下面条?我说,最拿手了。
雪停了,天空晴朗,好像艳粉街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
说实话,我从来没下过面条,但是我可以稍微试试,应该并不难。也许我们推门进屋,就看见父亲歪在炕上,炉火温热,他已经睡熟,那我就应该下三碗,每碗都有鸡蛋和葱花。
路途笔直,我拉起姑鸟儿手,沿着湖岸,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飞行家》(节选)
朗读者:程异

电影《刺杀小说家》截图,图片来源:豆瓣
程异:英文版《飞行家》(第二部分开头一段,有一小部分,不在沈阳,而在北京,所以我们可以先走出艳粉街一下。)
大姑打电话把我叫醒的时候,我刚刚睡熟。挨到凌晨三点,还是不困,就下楼买了一件啤酒,喝到第三瓶,终于有点困意,赶忙到床上趴着,也没有马上睡着,啤酒胀肚,五点钟起来撒了一大泼尿,才睡下。
北京的冬天不比家里,每天雾气昭昭,冻人不冻水,到了夜里从窗户缝里渗进一股阴冷,这啤酒喝得有点作妖,直打哆嗦,只好把自己深深地裹在被子里。
第二天是周六,约好了陪领导踢室内足球,我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司职右边锋,能甩牛尾巴,现在胖了三十斤,换好运动服就出一身汗,不过也没关系,踢球不是重点,重点是踢完球喝酒,喝酒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听领导讲他在大学时是个足球健将,左右脚七十米长传。
问题就出在,因为睡着得比较晚,以为得混到天亮,手机没有静音,清早七点半,大姑的电话打进来,我其实刚刚进入深睡眠,忘了自己身处东四环附近的一家出租屋里,腮帮子发紧,以为自己睡在家里那张硬邦邦的单人床上,后来单人床不见了,梦见自己在高考的考场,政治题怎么想也想不出,伸脖子想看别人的,别人都离我很远,且用胳膊把卷子蒙住,急得我想把自己脑袋揪下来。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我一激灵坐了起来。
哎,是小峰吗?
我一听就知道是大姑,虽然已经两年没联系过,但是她的锦州口音辨识度太高,尾音永远是挑上去,像唱歌一样,而且不说喂,说哎,好像对方接听让她觉得很突然。
我说,大姑啊。大姑说,你个死孩子,过年也不说给大姑打个电话,你奶天天念叨你。我说,大姑,我还没睡醒,一会给你打回过去吧。大姑说,别撂,大姑不是让你还钱,有正事儿找你。
04
声音,记忆,视角,叙事:
东北文学与东北学
宋伟杰:
雪涛和程异的双语互动,引领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出东北记,然后再回到东北。我们可以看到沈阳、东北的其他城市与北京的互动,也可以看到东北城市在过去或者现在,北京的诱惑、陷阱,还有其他的故事。下面我们进行第二轮,进一步讨论三部小说,东北、出东北,再回到东北,请罗鹏教授先提第一个问题。
罗鹏:
在提问之前,我先讨论一下作品可以吗?刚才Eric也谈到历史,我想回到《平原上的摩西》,讨论一下不仅是和历史,而且是和个人记忆有关的一些想法。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在《平原上的摩西》比较前面的部分,主人公之一李斐说,“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记忆开始清晰可见,并且成为我后来生命的一部分呢?或者到底这些记忆多少是曾经真实发生过,而多少是我根据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以自己的方式牢记的呢?已经成为谜案”。后来她又讲了一句,她说,“那个夏天的傍晚,在日后的许多个夜晚都曾被我拿出来回想,开始的时候,是想要回想,后来则变成了某种练习,防止那个夜晚被自己篡改,或者像许多其他的夜晚一样,消失在黑暗里”。
《平原上的摩西》中有两个很关键的概念,就是历史和记忆。这个小说同时回顾过去并且看待未来。我比较感兴趣小说是如何反映个人的创伤和群体的危机,还有赎回和重建的过程。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小说比较中间的一部分有非常关键的一段,主人公的爸爸李守廉跟她童年好朋友庄树的母亲傅东心。当时李斐刚刚小学毕业,傅东心去了李斐的父亲的家里给他一些钱,因为她知道李斐的爸爸刚刚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借给了另外一个人,现在已经没有钱付李斐的中学学费了。李守廉拒绝接受这笔钱,他后来为了付学费把自己一些文革时期的邮票卖掉了。这是个人跟历史的一个冲突。
这发生在1995年,是对他们两家而言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对国家历史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这一段也不仅强调时间本身,比如说傅东心到了李守廉的家里时,李守廉刚刚把一个挂钟拆开了,准备修一修,桌上裸露着挂钟的机芯,在哒哒地走着。后来跟傅东心谈话的时候,就专门描写了李守廉手腕上戴着一个海鸥牌的手表,他弄了弄表带。

电
后来傅东心对李守廉说,结婚生孩子之后,她发现文革时期她的先生庄德增杀死了她父亲的一个好友。李守廉听到这句话之后,他说过去了,现在不是这样了,但是他加了一句,“他说,过去的事儿和现在没关系,人变了,吃喝拉撒,新陈代谢,已经变了一个人,要看人的好”。
1995年庄德增去见李守廉的时刻,是小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那个秋天有好几个出租车的司机被谋杀了,最后一位是圣诞节当晚李斐和爸爸打车的司机,这个司机本来是警察,后来李斐受伤了。
这篇小说总共有七个叙述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警察流氓什么都有。我觉得他们的声音、语言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他们讲的内容区别很大,他们说的话好像是一种标准的书面语言。所以我想问的是原文也好,翻译也好,有没有考虑过给每一个叙述者一个特别的声音,帮助读者分辨?
双雪涛:
特别感谢罗鹏教授很敏锐地描述那个场景,我确实是把傅东心去找李守廉,李守廉在修一个钟这个场景,当作这个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写。钟确实是我认真选择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他修的应该是一个跟时间有关系的东西。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这个小说其实最开始我并没有想涉及这么多关于历史的部分。因为当时我其实写了几篇小说,但是都没有太复杂。好像你不写点复杂的东西,别人觉得你就写不了复杂的东西。所以我就想去写一个稍微跨度长一点的内容。它的起点是一个罪案,最开始《摩西》初稿第一稿的第一部分第一章写的是一辆出租车在路上飞驰,后备箱里装了一具尸体。这个部分我自己写得也很过瘾,但是第二部分就开始难以为继,我不知道第二个章节该写什么,然后我突然想到先把人物的背景写一写,就开始写庄德增这个人物。写完这个人物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小说应当这么来写,而不是像我最开始那么写。所以好像不是我选择了这个历史,而是某一种相遇,因为你想写的东西,让你不得不去了解庄德增这个人物的历史,你不得不去了解李守廉这个人物的背景。个人背景也难免要跟时代背景、社会历史相关联,不知不觉就掉到了历史的漩涡里。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当我初稿写完之后,我就把第一章出租车的部分完全删掉了,它就完全变成了一个从庄德增的历史开始的一个故事。所以刚才罗鹏老师说的场景,我觉得其实可以说概括了小说某一个部分的场景。因为我们经常太过健忘了,经常会为了活得开心一点去努力忘记一些事情,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大家的。包括庄树,最后李斐问他为什么你没有来,庄树说我忘记了。我觉得忘记和记忆确实是这个小说里我想说的东西。庄树并不是故意忘记了,他那天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去,我觉得这种遗忘是更残忍的,而李斐牢牢记得那天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正因为如此,李斐可能是这个小说的眼睛,因为她不想忘记每一个细节,她要不停地练习,去回忆那些夜晚,因此李斐是小说的双眼。
刚才您说的声音的问题,首先我当时曾经努力试过,想要写出七个不同的声音。但是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写好,另一方面因为那种结构的小说跟我心里想象的拉开了差距,不是我心里想象的东西,像一种话剧似的在模仿每个人的腔调,我觉得统一性会有点问题。所以必须做一个取舍——是想要一个平顺的、统一的、但也许不是那么真实的一个作品,还是要努力去还原真实,达到大家可信、但不是那么统一,而且会造成交流的壁垒的作品。不但是跟读者的壁垒,也是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壁垒,因为当你看到每一个人物的叙述声音有极大不同的时候,你会怀疑他们能不能顺利交流。
所以取舍之后,我决定用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现实的一种方式,每一个人的声音节奏几乎是一样的,但仔细读这个小说,会发现每个人内心节奏是不一样的。我放弃了模仿外部的声音,而用一个统一的外部声音去表达内心声音的不同,我觉得这个可能能够达到我想要的预期。这也是最后我做的选择,以这种方式讲述对我来说也是比较舒服的。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程异:
我第一次读雪涛的小说就立刻感觉我们不是在一个现实的世界。我的想法是,在雪涛的小说里,艳粉街不是一个空间,而是一个概念,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状态。这些人物都被封闭在这个状态里,所以叙事声音统一对叙事方法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会感觉到很封闭,在一个很小的世界,而每个人都走不出去。
作为译者,我的责任就是跟着作者,如果作者对声音没做太大的区别,我也必须跟着。我感受到的声音是雪涛的,这是很明确的。我的想法就是雪涛作为作者,是从每个人物的内心里、从他们的眼睛里看世界,可是声音还是他的。所以我就跟着这声音直接译成英语,所以其实没太大的区别。可是雪涛说得对,还是感觉出这些人物内心区别是很大的。
宋伟杰:
我觉得声音不单单是叙事的声音,还有可能是东北的口音。我觉得Jeremy讲得非常好,那可能是一种心理现实状态,通过什么样的叙事策略把它展现出来,制造出来,这不仅是东北的现实写作,更是一个心理状态的幻境、梦境式的描述,这是非常精彩的。
王德威:
在周一,我的一些学生在班上讨论过声音的问题。我想刚才Jeremy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就是我们不需要依赖着所谓现实主义的摹拟式的声音状态的复写。双雪涛其实经营了一种人物之间的互动,哪怕声音略有相似,但是每一个人的节奏还有基本语境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营造了不同的叙事状态。这个状态不需要和现实主义所谓的什么声音配什么样的人,配什么样的情境,而刻意做出对比。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呼应了双雪涛在文字风格上一种实验性的尝试,而且不只是在《艳粉街》里,在其他的(作品中),像我个人最喜欢的《走出格勒》也是类似的,几个人物其实是可以分辨的。Jeremy作为一个译者,这样敏锐的诠释我是佩服的。
我们从东北的立场再请张学昕教授做第二轮的发言。
张学昕:
刚才说到叙事声音问题,雪涛说他不太顾及那种喧嚣、骚动、嘈杂,但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年莫言写的《红高粱》,在开始的时候用了“我爷爷”、“我奶奶”,在雪涛的叙述里边也经常说“我姑姑”、“我哥哥”、“我妈妈”等。其实这个角度就是非常个人化的,这个角度压住了种种驳杂的声音。

电影《红高粱》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这些人可能是讲述,也可能是被讲述。无论讲述和被讲述,这里边都贯穿着雪涛的一个人的统摄的声音,这种统摄的声音无论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在空间维度上或者在时间维度上,都是由雪涛自己的叙述来统摄的,这种统摄形成了叙述主体对被叙述的一种控制。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说家必须具备的能力。
这个能力也是一个叙述的伦理,这种伦理直接影响写作的形态。声音直接跟叙述视角有关,视角(小说创作的政治学)和声音决定了雪涛小说的形态和结构。所以我又回想起当年黄子平他们写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强调20世纪中国文学的荒寒,荒寒是一种美学特征。我觉得在雪涛的小说里,包括班宇的小说里,都体现出一种荒寒美学。它是一种由被压制的向下的东西往上看。无论是《摩西》里的一些人物,还是《飞行家》里的人物,以及牧师的死去,都有一种离去、飞升。雪涛的叙述其实控制了整个的叙事格局。
电影《平原上的火焰》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我记得2019年在大连开东北学会议的时候,德威老师提到了文学东北的问题,把雪涛、班宇、郑执们的创作纳入到文学东北以至于东北学的范畴,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就是我想说的,呼应德威老师的文学东北和东北学。
新东北文学是什么样的?我记得当年在大连的会议上,我和华东师大黄平教授还做了一个交流,他当时也响亮地提出新东北学的概念,新东北学的概念新在哪里呢?它不是一个《铁西区》的问题,不是一个所谓“三剑客”。我否定了“三剑客”这种说法,把“三剑客”捆绑在一起消除了它的异质性,这是不妥的。新东北应该还包括黑龙江,包括吉林,但现在重心却由双雪涛、班宇、郑执几位来完成和实现这一次突围。

从左到右依次为:双雪涛、郑执、班宇,图片来源:网络
包括再往前呼应,像萧军、萧红、端木蕻良,以及后来迟子建、阿城、金仁顺、李铁他们的创作,双雪涛他们接续了,也试图超越。我觉得双雪涛小说都具有一个巨大的隐喻,这种隐喻不仅是艳粉街,而且是一个庞大的对社会生活、对人性、对一个结构的隐喻。
所以我觉得藏在双雪涛作品审美后面的第二项更有待于我们挖掘。一方面我们刚才在文本细读层面做了更深一步的梳理,我觉得从大的层面来讲,新东北文学的重建、对前辈作家如何超越,历史责任宿命般地落到了双雪涛、班宇们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德威老师倡导的东北学还要继续,文学是它一个重要的分支和脉络,我想呼应一下2019年大连“东北学”会议上我们当时的一些构想和研究的走向。
王德威:
我想跟线上的观众也说明一下,我和宋伟杰教授正在编选一本《东北读本》。《东北读本》可能依照不同的客观情况有不同的版本,我们希望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读本,系统地向读者介绍20世纪初一直到当代像双雪涛等等作家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及他们跟东北这块土地的一种休戚与共的关联性。非常谢谢张学昕教授的说明。
05
无私的工作,电影的力量
宋伟杰:
《平原上的摩西》改编成的电影,延迟放映。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一直在推介重要的作家、艺术电影导演。我们希望请崔峤女士讲一讲文学电影改编,关于艺术电影的想法,并进一步和雪涛对话。
崔峤:
谢谢各位老师。我最开始看到双雪涛小说的时候,第一个感觉,他是非常极致的理想主义者。他以不同的角度去进入文学——他以前做金融行业,现在很多作品又跟电影圈发生了互动,甚至电影创作跟他的文学创作也是平行的轨道,各有各的表达。
我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工作的时候,2002年做中国选片顾问,当时选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王兵导演的《铁西区》,分为三部,第一部叫《工厂》,第二部叫《艳粉街》,第三部叫《铁路》。当时我们看了这三部电影之后,邀请第二部《艳粉街》去了2003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全世界都非常关注,这样的内容和题材也非常勇敢。
《铁西区第二部分:艳粉街》海报,图片来源:网络
但是我听王兵跟我讲过很多这个电影后来在中国的一些遭遇。2002年到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包括我们前一阵也关注吉林的疫情,整个时空也好,文学也好,电影也好,其实都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我也很想听雪涛讲一讲,因为你在每一个系统里面都很游刃有余,同时又很超脱。
你现在的自我挑战到底是什么呢?
双雪涛:
谢谢崔峤老师。我第一次知道王兵老师的《艳粉街》跟您还有这样的缘分,因为我觉得电影三部曲是非常伟大的,尤其到了现在,越来越觉得它保存的东西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我其实不太敢看完,我都是看一看停一停。因为我特别怕在《艳粉街》部分里看到自己,因为他拍摄的期间正好我也在艳粉街住着,我怕突然一个拐角我自己走出来,虽然很惊喜,但也是很恐怖的事情。

电影《铁西区第二部分:艳粉街》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我觉得作为文学来说,不能说挑战,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想法。我还是觉得文学虽然是一个公开的私事,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去做这个事情的,但是我越来越觉得需要更多地去看到别人。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里,我觉得比较缺乏的是“无私”的工作。
因为每个作家都是从“自私”开始写作的,怎么能进入到一个比较“无私”的工作?这个是比较难的,也是我这一两年在考虑的事情。包括比如王德威老师做今天这个活动,包括在座的每个朋友,我觉得都是有无私的部分。可能在国内做文学也需要有同样的心态,这个就是在创作之外了。我觉得创作本身其实很难聊我有什么样一个目标,但是我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创作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也是我最近在想的事情。可能今年或者明年会去把它付诸实践,也许是一连串的活动,或者是集中做的东西,看看能不能为文学做一点工作。

双雪涛,图片来源:网络
这个电影行业是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一个是疫情的原因,一个是资本的原因,还有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包括我看到美国电影也受到了不同的挑战,也包含着意识形态的问题。包括创作,一旦被很多东西所束缚的时候,它肯定会产生一连串的问题。
但是我一直相信电影的力量,包括我跟很多电影界的朋友也一直保持沟通,我觉得电影是一种直观的艺术,这种直观的艺术能够一下子把想要传达的东西传达给别人。我个人认为国内电影可能更需要做的是小规模的,做比较个人的、作者的,从这里开始慢慢培育更多好好做作者电影的人,慢慢再去输送到电影各个环节里。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想法。
王德威:
现在有线上来宾的一些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选择一些,看看是不是雪涛或者Jeremy愿意回答。
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请问双雪涛先生如何看待东北文化?你既然来自于东北,现在到了北京,甚至会说满洲文化、满族文化水土的流失,那么现在东北文艺复兴是不是一种最后的突围呢?新东北文学是不是从此就走向了荒芜?
双雪涛:
首先我觉得东北文艺复兴这个帽子扣得大了点,因为我们远远还没有复兴,还有很多路要走。一个地区的地域的文学想要走得远肯定不是几个作者就能做到的,需要连续不停地诞生好的作品。(文艺复兴)包括各个层面,也包括泛文化领域的东西,而不光是文学创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才能叫做复兴。
另外一方面东北文化其实我觉得是移民的文化。我的爷爷是一个北京人,我的姥爷是一个山东人,所以它的根须到底是什么?这些人最后怎么都变成了东北人?我觉得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东北的集体主义大家也都知道。在建国之后的工业改造中,大规模的厂矿和工厂,我觉得在某一方面大大型塑了东北的历史,或者大大型塑了东北人的性格。东北人的很多东西是在移民文化和集体主义的改造下一点一点融汇起来的,我也很难总结它的核心是什么。

电影《钢的琴》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包括东北的语言,其实有很多正在消亡。比如我妈妈在说的一些语言,有时候我回去一听觉得太妙了,但是真的很少人会说了。因为它可能有满语的部分,有工厂行话的部分,还有一些从影视剧来的变体,比如赵本山对整个东北语言的改造,我觉得他的创作其实某一方面在改造东北的某一种口语。这些东西融在一块,使得东北语言非常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如果大学宿舍里有一个是东北人,很快大家都会说东北话,它的传染性和感染力非常之强,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语言。

电
最开始使用东北口语并把它变成书面语的过程,是我特别有乐趣的一个部分,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非常之大,就像虽然都是猫科动物,但是有一个是猫,有一个是老虎。但这个过程中,打捞这些语言把它变成书面语是我很大的一个乐趣。
这个问题可能也需要很多东北的写作者去一起做,而非只是一两个人做,因为这些语言丢了就没有了。包括我昨天在写东西,突然想到一个词儿叫“歇咧”(蝎厉),这个人咋这么“歇咧”呢?我不知道王老师能明白这个词儿哈(王德威:我明白,蝎厉),“歇咧”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咋这么娇气呢,怎么还没咋地,你咋就哭了呢。但是我自己的东北的语言都在流逝,这挺可惜的。如果有所谓的复兴,可能得从这些小小的工作开始做起。
06
风格的魅力,类型的启发,语言的骨头
王德威:
回答特别好,特别恳切。
下面有三位线上来宾都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双雪涛作品里面的宗教成分,最直接的问题是你本人信教吗?摩西到底是怎么来的?或是你对于东北现在宗教的层次、广义的宗教面向有什么观察?
双雪涛:
这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很难的问题,我特别想说自己是一个信徒,但我不是。在我从小受到的教育里,大家可能也从我的小说里能够了解东北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在这种教育体制下我很难成为一个有神论者。但也可能是缘分和机缘还没有到。
另一个层面,为什么这个小说里会有宗教的元素?我每一次去读《圣经》里的段落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鼓舞,我一直把那种元气充沛的故事当做某种story形态,但这种形态是如此地自信,如此地不容置疑,而且带着一种传播的热情,这种东西对于小说来说简直是天然的契合。
另一方面,我的小说没有那么现实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一些东西去固定,把它像一个脚手架一样先搭起来。尤其在2015年左右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我经常会想到与宗教有关的故事,包括约拿的故事,水里的故事(比如光明堂的故事),包括摩西劈开红海的故事,信念的故事,包括诺亚方舟带大家逃离,保存自己有生力量的故事。这种嵌入使得我对我自己的故事的把握会不一样,每当我提起这些宗教里的故事的时候,都会使我想到关于这个故事的更多的意蕴,这使我能发展出更多的东西,对我的启发是不可言说的。所以可能在文学上,我是宗教的信徒。
王德威:
这是加州大学的一位博士后学者,她提到您过去的影评到剧本,从早期《翅鬼》到悬疑甚至“黑色”小说,比如《跷跷板》和《摩西》,再到最近2021年在《人民文学》发的作品等等,她注意到你的小说写作里对文类的运用,想请你谈一下你对文类的选择跟你个人的信念是什么?
双雪涛:
首先我不太喜欢去做一个无聊的东西,我在很多类型文学里得到了很多营养。就像加缪说的,他在詹姆斯·凯恩的《邮差总按两遍铃》里得到了《局外人》的启发,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在读很多类型文学时受到的启发都很大,这个启发是故事链条的第一方面,就是故事要往前走,这个链条怎么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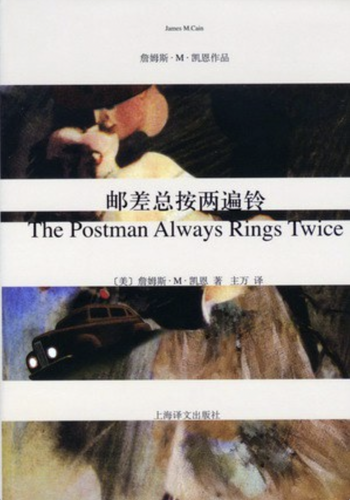
书《邮差总按两遍铃》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另外一个是人物怎么塑造。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喜欢金庸,但现在再看可能感觉不一样了。我在少年时期对他的迷恋是非常恐怖的,每天都要看一段,因为他的故事和人物实在是太精彩了,对人物对故事本身的迷恋一直在我的血液里已经挥之不去了,这两个部分在类型文学里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而且我一直认为中国大陆文学的一个问题,就是对类型文学的重视不够。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充分的类型文学的发展,有真正的以类型文学为志业的写作者,我们的严肃文学一定会变得更好。但是可能因为我们在这一块比较缺乏,老是觉得文学应该高级一些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它就变得很贫瘠。
另外,我也常受到黑色电影的启发。很多伟大的经典电影其实都借鉴了非常多的类型电影的元素,比如《教父》、《闪灵》,包括伟大的黑色电影《M就是凶手》,你很难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这个可能也是我在文学里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不想被归类成某一种类别——我是严肃的还是其他的。我觉得文学是用抽象的文字和别人沟通的一个艺术,自我标榜没啥意思,需要看真正的读者、优秀的读者阅读它的感觉。

电影《闪灵》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王德威 :
一位在吉林的线上观众,他说自己回到东北工作。那么请问双雪涛老师,你对于东北居住,或者将来你要怎么样决定你创作中所谓的主体位置?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多半时间都是在北京或者在所谓的关内地区了,你怎么去保持对东北创作的敏感性?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还有一连串类似的问题,关于你最近的小说是要离开东北、回到东北、还是悬置东北?
双雪涛:
谢谢王老师一直在辛苦地摆渡问题。首先我觉得住在哪和写什么不是一个紧密的逻辑(关系),我住在不在东北的地方,就一定写不了东北,我觉得不是这个逻辑。这个不像钓鱼,你必须得在那个地方钓,才能钓出鱼来。
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在东北活了三十几年,想变成另外一个人已经变不了了。我只能永远带着这个基因带着这种思维方式在世间存在了。但是就地域而言,我现在回去其实觉得我的家乡沈阳已经变成了一个跟其他城市区别不大的城市,至少在面貌上。艳粉街已经消失了,变成一片住宅楼了。我小时候玩的街区也不复存在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某一种个性。
但是我的那些玩伴,和我一起成长的人,他们还在那里,我也经常回去跟他们约见一下。我会时常回去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让我为了写东北要住在东北,我觉得这个招式可能有点难。
另外,是不是一定要写东北,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第一点是我写了不少东北,我不能说自己写够了,当我再想写的时候肯定是因为我想写。我最近也在写一个关于东北的故事。你控制不住有时候经常会回去,但是也会写一些其他东西。我一直觉得地域,就是我出生在哪儿或者每个作家出生在哪儿,特别容易被人作为一个概念去理解,我也特别欢迎这种理解,因为这种理解可以使你的文学被更多人了解。
但是另一方面它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对应关系,任何一个作家不可能因为他的出生地而了不起,正是因为永远保持可能性,所以我们还在文学上可以做一些工作。
王德威:
还有一个问题来自香港的崔文东教授,牵涉到你个人的兴趣,他说对你而言,在中国或者是西方有没有一些你个人心仪的无论是现代还是当代的作家?有没有成为你在写作上的影响或者来源?
双雪涛 :
如果列举对自己影响大的作家,会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我就挑几个节点。
我最开始领略到文学的美丽或者西方文学的美丽,是海明威的《杀人者》。是我在一个包装很艳俗的读本里发现的,它非常短,就像一部黑色电影一样,有很强的镜头感和非常简练的对话,讲述一个少年对于罪恶的一种发现。我当时特别震撼,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后来我每每看到海明威的小说都会去看。但客观地说,我不能说海明威的每一篇短篇小说都非常好,但确实有几篇小说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他强烈的风格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风格是如此的迷人,如果一个人具备了某种风格,他就会很charming,他对我的诱惑力就像是口红对于女人的诱惑力。
书《杀人者》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第二个是我在高中时期读了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中国很多作家语言里总有一种革命性的语言,我觉得阿城是少有的这种东西比较少的作家,他有一种俗世的语言,有一种带骨头的语言,从《水浒》、从明清笔记小说来的语言,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新奇的。它如此生动,它的动词那么的有力量,它对我的感染力是非常强的。让我明白在风格之外,这个语言就像骨头,一定要有语言的骨头,才能立得住。这种感染力也影响到我现在的风格。

书《棋王》《树王》《孩子王》封面,图片来源:豆瓣
我现在正在读何伟(Peter Hessler)的《寻路中国》,我特别喜欢,这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写的《江城》和《寻路中国》,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角度,能够让我也从某一个方面重新理解我生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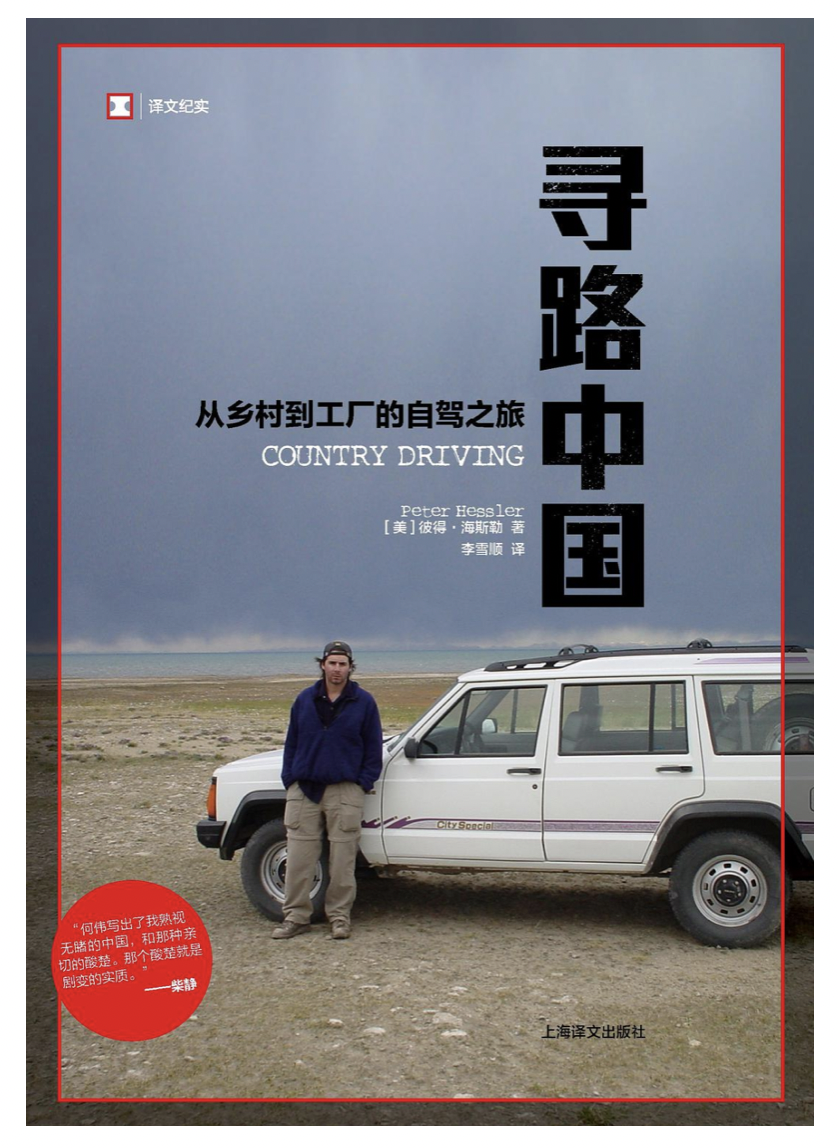
书《寻路中国》封面,图片来源:豆瓣
宋伟杰:
刚才的朗读让我有点意外,雪涛选的是《光明堂》的一段,而程异选的是《飞行家》的一段,《平原上的摩西》的结尾非常强,但是你们都没有选!东北研究现在很重要,很多年轻学者,包括刘岩、黄平、丛治辰、刘大先,都让我受益匪浅。《摩西》结尾的那些物、物象,既有诗意又有叙事力量,尤其是那个平原烟盒。他握过的手枪和烟盒,一定都带着体温的,是日常的用品。烟盒上的图案是一个少女,是青春记忆,是一个理想的过去。我当时的第一个直觉就想到了是贾樟柯,《三峡好人》里面的矿工韩三明,他看着人民币,人民币也是一张纸,像烟盒一样的纸,它的背面是夔门。在他面前是真实的地理场景,和纸币上的场景有了一个对应。
电影《三峡好人》截图,图片来源:豆瓣
所以我在想这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物,比如说飞行器,比如雪涛提到的树和雕塑,包括《刺客爱人》里面战国的宝剑,背在身上,也会有一个身体的温度,这样的话题我们就不用多讲了。
但我想到这里面有一个叙事动力的问题。比如说你读阿城,而你的小说里面的人物也是比较特别的,虽然都是小人物,但都是奇人。像阿城所写的那样,他们有他们的风范和风度,有他们的固执和对一种价值观念的固守,这不是一般的普通人,而是有一个特别的叙事。你说你喜欢金庸,这是一个说法。你也喜欢徐皓峰式的侠义叙事——回到民国,那种特别的规范、风度、范儿,哪怕受苦、受难、受辱,但还保持那个范儿和风度,你非常想写平凡但也是奇特的人。
悬疑叙事我觉得非常精彩,《摩西》是非常好的一部作品。悬疑是一种考掘,要把空间意义上的“跷跷板”下面的尸体挖出来;它是一种考古,把时间意义上东北的过去,无论是毛泽东时代或者更早的东北的过去和现在放在一起;它是一种细读,必须要把所有的蛛丝马迹和犯罪的可能都重新组合在一起,把一个案件变成小说的一个故事;同时它是一个拼图,是一个编织故事的过程,把所有的老工业基地解体前后、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拼成一个全景图。
所以这就回到我的问题了,因为你说写小说,中篇或短篇,一定要找到一个让你兴奋的东西,兴奋的东西可以看到小说的力量。所以我就想几年以后,如果你重新看这三部被精选后翻译成英文的中篇作品,还有哪些让你现在还是很兴奋的、很难忘的瞬间?除了这三个作品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作品,到现在你还是念念不忘、感到兴奋,重新讲述东北或者东北之外的记忆和故事?
双雪涛:
我很少重读自己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好像就看自己的裸体一样。上次也是要做一个活动,不得不读一下自己的小说,我就看了一遍《平原上的摩西》,我觉得当时还是饱含感情的。然后顺便看了一眼《大师》和《走出格勒》,因为都在一个小说集里。当时因为手边没有,我就在人民大学的图书馆借了一本,看到《大师》的结尾真的是把自己看哭了。我估计旁边的那个同学一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他怎么在这儿哭了呢?而且她要是知道我在看自己的书,就会觉得更奇怪(众人笑)。
那时候的写作我确实投入了很多的情感,可能现在因为写的时间长了,情感浓度不可能保持那么高,那么高的消耗实在太大。但当时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那些我觉得不是某一个桥段,我觉得最主要是情感,包括《走出格勒》男孩一定要背着尸体走出去,我觉得那种情感可能会感动到现在的我。
王德威:
我必须要加上一句,我们线上的来宾有一位在阅读《平原上的摩西》看到后来也看哭了。刚才广州的中山大学的林峥教授说双雪涛是一个有情的作家,令她感动的一位作家。
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可以继续聊下去,今天真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要特别谢谢编辑Brian的主催,让英文版《艳粉街》能够顺利地在4月19号上市。感谢所有的嘉宾,线上的来宾,今天我们的时间确实超过了原定的时程,看到这么多的观众一直留守到最后,特别感动。我们想在线上所有的来宾可能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期待双雪涛更精彩的作品,不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除了写剧本之外,别忘了继续写小说好吗?(众人笑)
双雪涛:
一定一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