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承桃:物的批判

新声 NEW VOICE
支持青年人才,为新的梦想共声
由40位伯乐举荐十大创意领域的40位潜力新锐。
由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财新视听、CX创意联合发起的《新声——中国新生代艺术家推新计划》,旨在支持青年人才,为新的梦想共声。
我们邀请来自艺术、设计、电影、建筑、思想、文学出版、舞蹈、戏剧、音乐、美育等领域的专家伯乐,推荐他们最注目的年轻创作者。他们或因奇思妙想、大胆突破而醒目,或有着拔群的锐气、睿智,或凸显出某种当下罕有的质地。他们的成长路径和个性化选择亦可折射时代的特征,他们的先锋、原创、个性,代表了BCAF一贯支持的真实思想表达与多元对话空间的理念。
新锐创作者将获得BCAF及财新传媒各渠道、全网传播的推广合作,也将优先获得国际交流、创作资助、艺术驻留的机会。
第二季10位新锐的深度访谈文章、人物纪录短片自2022年10月28日起,在每周五17:00持续发布。
新声 NEW VOICE第二季第五期 | 易承桃(艺术家)

新声伯乐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伯乐推荐语:
易承桃是一位具有综合背景的新晋艺术家。出色的工业设计技能和良好的科技训练,使他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多向度的思维模式和成熟清醒的批判意识。从他初露峰芒的艺术作品中,展现出年轻一代艺术家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令人感受到新艺术的气息。
刘家琨
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伯乐推荐语:
易承桃是一位具有综合背景的新晋艺术家。出色的工业设计技能和良好的科技训练,使他具有跨学科的视野、多向度的思维模式和成熟清醒的批判意识。从他初露峰芒的艺术作品中,展现出年轻一代艺术家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令人感受到新艺术的气息。

▲ 新声 NEW VOICE第二季第五期 | 易承桃(艺术家)
每周有三天,易承桃会从新泽西州的家出发前往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工作室,搭上Path快线后转乘地铁,一个多小时的通勤时间使他从日常工作中抽离出来,发呆、放空、观察形形色色的人。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流浪汉在地铁站里抓着公共电话大声吼叫,易承桃好奇驻足,心想他在吼什么?到底有什么紧急情况?电话筒的另一端有没有人在听?还有一次,他在世贸中心地铁站换乘时,看到一只闪闪发光的蓝色鞋子卡在铁轨之间,为什么一只奢侈品牌的鞋会在脏兮兮的轨道上?这只鞋的主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列车压过轨道,刹车的金属摩擦声与此起彼伏的交谈声相互交织时,颗粒般闪烁的思绪微微抽动他的脑部神经,若有若无地捕捉这座城市带给他的灵感。

▲ 易承桃在纽约世贸中心地铁站看到的鞋子,图片来源:易承桃
易承桃从小喜欢工具、电子产品,大学时去纽约的普瑞特艺术学院读工业设计,除了接受功能性、生产技术上的训练,他也上雕塑课,受到古典主义形态的熏陶。学校推崇批判性思考,生产和美化产品并不是首位,反而要求学生对固有的生产系统有一些反思和对抗。

▲ 易承桃在布鲁克林的工作室,对于他的创作空间,在家是数字上的生产,工作室是体力劳动,图片来源:易承桃
2016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国一年,当时他脑子里盛满了想设计的东西——椅子、刨笔刀、记事本、筷子,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欲。他先在脑子里构思,然后用电脑做渲染图,所有作品由软件精心打磨,闪耀着光滑或磨砂般的质感——喷绘了印象派画家莫奈作品《睡莲》的机关枪、狮身人面像式的游戏机、抑或是将杜尚的小便池作品《泉》改装成赛车形状。这些物品似曾相识,但又不知为何而用。有的时候他上厕所突然灵光一现,摸到电脑桌前花一到两小时就做完了,有时候会需要一两个月的思考和打磨。每做完一个,他就和父母、朋友分享,一开始只是创作欲的宣泄,日记记录式地发在网上,慢慢地,这成了他持续五年的艺术项目《固态诗》。

▲ 《固态诗 #242》,2019年11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 《固态诗 #196》,2019年1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 《固态诗 #223》,2019年9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抱着对科技、新媒体的好奇心,易承桃去了纽约大学互动电子媒体实验室念研究生。在那里,飞行员、华尔街交易员、艺术家、设计师、运动员、舞者,各色各样的人一起共同实验、创作。毕业后,易承桃在某大型科技公司工作了一年,科技公司对消费品经济的关注、对产品销售增长率的痴迷,使得一切都变成了营销,完全市场化导向的工作模式令他感受不到纯粹的设计创作,商业上对效率的追求限制了他的认知感受和自我表达,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2020年,从科技公司辞职后,他决定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
从工业设计师到艺术家,易承桃的身份、创作纯度和目的都在发生变化,但始终未变的是他的问题意识——“我是90后,我们这一代人是什么样子?我在面临什么时代和社会?作为这个年代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对自己和大的叙事之间来说意味着什么?”
快问快答
Q:现在在哪里?生活受疫情影响大么?怎么调节?
A:我现在在纽约。之前疫情期间,我搬去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城坦帕(Tampa),呆了一年半左右,现在又回来了。我刚刚得了新冠,第一次,现在还有点症状,快好了。
Q:你觉得当下最亟需改变的人类社会现状是什么?
A:我们的思维、感受日渐麻木,但是情绪却愈发极端。我能感觉这种情绪在慢慢影响我。输入和输出不是很平衡,自我物化的进程感觉很快。在美国,伦理道德上、政治上越来越偏激,但是感受或同理心上越来越麻木、单一,很两极。
Q:你从事的职业能够有助改变这个现状吗?
A: 我会尽力尝试将问题意识带到我的艺术创作中,但我觉得我不能改变这个现状。可能我做的艺术也不是为了改变现状,而只是给予它足够的重视、关怀和诘问,让这些问题可以更显眼、更迫切。大家的专注力在那个上面的时候,或许会有得到解决的空间。
Q:你最想改变的个人现状是什么?
A:想比现在更自由自在和自如。
Q: 你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A:书、杂志、新闻网站、社交网络、网络视频博主,B站up主,YouTuber等等,非常杂,也不挑,能捡到的都会吸收,订阅很多,也看很多。
Q: 最近关注的艺术家?
A:极简主义艺术家Carl Andre、新的艺术家是Nicholas Lamas。
Q: 你的童年震撼和缺憾是什么?
A:震撼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初三,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可抗力,就觉得所有的意义和既有的结构很不堪一击,一切都可以倒塌,感觉很恐怖。至于遗憾,我童年没什么遗憾,很完整、无忧无虑,我一直觉得是我最大的幸运。
Q: 你的什么喜好会导致你与多数同辈人玩不到一块儿?
A: 我还是很喜欢和同辈人玩,只是有些时候跟不上潮流的话题,还有很多生活的细枝末节,我可能会慢半拍。更多时候我比较喜欢和上一辈的人交流,听他们谈论事情,我会感觉很惬意、很放松。
Q: 你第一次挣钱是做什么事?
A: 小学的时候卖画给同学,一开始5角钱一张,后面能卖到5块钱一张,感觉很有成就感。
Q: 如不必考虑生存,你的创作/工作会与现在有何不同?
A: 之前是做职业设计师,现在全职做艺术,也算是靠艺术谋生了。不考虑生存的话,我的创作还是会和现在高度一致。
Q: 你睡前刷多久手机?有被某种意识裹挟的时候吗?
A:会。我深夜就会接近病态地刷很长时间的手机,明显能感觉到我是被手机即时内容所裹挟的那种人,喜怒哀乐也很容易被看到的新闻影响。我很常失眠,我觉得我的意识和关注力是被手机殖民了的这种状态,很悲观,也尝试在改变,但深夜我真的很容易一刷就刷很久。
Q: 去年最高兴的事?
A:没有最开心的事,每次读到好的书,或者接触到新的想法,看到好的电影、好的作品,都会觉得被滋养了,就觉得很好,会开心一两天,但是这种感觉对我有点逐年减少,没有之前的感觉强烈,可能这两年好的文艺作品不太多。
Q: 作为艺术家,你最看重的三个品质是什么?
A: 真诚,刻苦坚持,还有一个是比较习惯性地具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
#01
从热衷买买买到警惕消费主义
B:为什么你会想学工业设计?
易承桃:小时候喜欢苹果、索尼,电子产品,汽车,对工具生产非常敏感。我是文科生,理科不是很好,就觉得我能够切入的角度就是设计,特别是工业设计能够同时把传达、关注、美学、硬性的生产工程都能够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学到就赚到的、很贪心的一个专业。
B:你去了Pratt艺术学院,美国的工业设计的教育理念是什么?你在那受到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易承桃:有非常系统的功能性、使用性、生产技术的训练。很怪的是Pratt也有很多传统雕塑的训练,叫你做很多现代主义的雕塑,对形态有一些非常古典的训练。同时也有批判性的训练,让你对系统有一点对抗性,不一定像很多其他学校学完就马上去生产很漂亮的产品。原来我还抱怨过,觉得不够强,专业不对口,但是后面慢慢会觉得它其实也给学生留有余地,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也有影响的地方。

▲ 《固态诗 #140》,2017年10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固态诗 #292》,2021年1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B:你在苹果实习,在微软工作过,喜欢这两个经历吗?
易承桃:在这种大公司、科技公司的科技部门工作,能够长见识挺好的,同时又加剧了我的紧迫感。当时一下子意识到可能我不太适合这样一个工作模式,不能再坚持下去了,不计后果想要离开。
B:具体是什么紧迫感?
易承桃:在一个大公司,唯一的目的是对它的股东负责,它只关注增长。于是一切都变成了营销。设计在里面的位置是什么?我很多时候都会感觉到岌岌可危,它可能最后是一个营销的结果。虽然可以通过资金、人力、剥削等等,把这个结果弄得非常美,但这期间所产生的很多东西是我可能难以琢磨甚至不认同的。

▲《固态诗 #262》,2020年8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固态诗 #273》,2020年10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B:你的很多作品在探讨消费主义,你之前从事消费品设计的工作对你个人的消费观或物欲,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易承桃: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他们见过物欲最低的一个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会买玩具,不断地买,还没收到,就开始订购下两个了。我完全不知道是我想要这个玩具,还是在享受订购的多巴胺的分泌。大学毕业之后,我的物欲就不强了,可能是知道了事物从生产到被使用到最后消亡的过程,对拥有它比较难提起兴趣。我更享受创造一个东西的快感。拥有,在很多时候是买东西的时候最兴奋,但是开包后很空虚,这种东西让我很警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一直对物品和商品保持冷眼的态度,我的作品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B:这些影响,对你的艺术创作起什么作用?
易承桃:我喜欢关注人和物体的关系:商品怎么影响我们,拥有它、使用它意味着什么,被它包围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它。我们已经身处商品主义文化、消费品文化中间的时候,怎么面对它。很多时候,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消费关系,而有了文化上的控制,你是不是也变成某种商品?甚至是商品之外的艺术品、武器,所有这些物体,都是我想关注的。

▲ 《固态诗 #237》,2019年10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B:《固态诗》系列是从2016年到2021年,一共314件作品,什么契机让你开启这个项目?又决定结束它?
易承桃:我想要生产一些好玩的东西,也做不出来,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欲,就觉得那就先做假的,先做渲染,做图像,是以这样的初衷去展开的。有很多当时对工业设计的思考,对消费主义美学、形态和功能性的很多疑问杂糅在项目中。
我是2021年,去年结束这个项目。它帮我完成了一个从设计师到艺术家的身份与视角的转变。我的很多疑问也变成了我的立场,新的立场、新的思维就需要新的作品来展开,所以我觉得是时候结束它,这些作品帮我带到了现在的处境。
B:具体是什么疑问和立场呢?
易承桃:工业设计是一个永远在和消费主义、美学、创作、人际、功能等各种因素不断扭打的结果,最后我的立场还是在创造这边,和消费主义稍微对立。还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比如什么是人文精神、争议、真善美,所有的诘问都能在创作中找到自己的立场。但是《固态诗》可能已经到达某种它能承载的天花板了,我需要有新的语言去阐释新的东西。

▲《固态诗 #302》,2021年2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 《固态诗 #230》,2019年10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B:为什么第296件作品说“警惕极简主义”?
易承桃:这是一个车床中间的传送带,意思就是大规模机械生产。因为极简主义这个词汇已经被劫持了,感觉好像很美,很佛,很日本,很轻,但它其实是一个大规模生产的复制品,要做到标准化,要节约成本,所有这些生产者觉得合适的东西汇聚起来成为了一种消费美学。但它又没有很多表达,也没有很多人性和温暖在里面,本质上是一个大规模生产美学,是在现在有限的生产能力下的唯一的美学出口。推崇极简主义,去神化它,把它和某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是我觉得该警惕的地方,所以我就把它们印在了大规模生产的车床带上。

▲ 《固态诗 #296》,2021年1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B:你真的去读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吗?你的设想中#293是一件什么样的产品?
易承桃:真的有读,平时也算是爱好,最近会读周濂老师的书《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也不是说我要去钻研马尔库塞,而是读到了,产生了对比,就将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作品的材料。这个作品也有点调侃的意思。3M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品牌,所以将这三个人物连在一起。这个东西看上去像一个产品,长着一副好像特别有用的样子,其实也没用,不具备明显的功能。

▲ 《固态诗 #293》,2021年1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B:这个项目持续了五年,其中有阶段性的变化吗?自我表达上或是对事物的观察上?
易承桃:可能有几次阶段性的变化,最大的区别是从一开始对审美形态上的陶醉和纯粹的创造欲宣泄,到后面变成批判性的创造。对于符号来说,人文,运用的语言也好,涉及到的话题也好,都会有很大的变化。从一开始我要设计酷的东西,或者我要探讨什么好看,会慢慢变得更复杂。
B:具体从哪件作品开始有一个转变?
易承桃:有一把绿色的枪,枪上有一个流星花园。这是我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想出来的。之前也没用过很多既有的、档案式的图像,我一直特别喜欢武器,对它抱有比较矛盾的感觉,想将这种暴力的玩具和流行文化揉在一起,当时可以说是无知的创作。但是却为我很多作品并置(juxtaposition)元素的尝试开启了一条较新的方式。

▲《固态诗 #169》,2018年8月,图片来源:易承桃
B:有人邀请你将其中一些作品生产出来吗?
易承桃:很多朋友其实都问过,只是我还没有做出那一步。我觉得它们现在在虚拟的展厅里,以图像的方式去呈现,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了,本来初衷也是这样的。如果被实体化,真正制造出来,很多东西可能在我这里会崩塌掉,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02
从实体到虚拟版图的创作
B:2020年,你的作品《XXX屹立在大地上》参加了史莱姆引擎策划的展览《版图》,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虚拟空间的展览吗?
易承桃:是的,他们邀请我做一个新作品放在这个虚拟展览里。我觉得也挺酷,我童年很喜欢新世纪福音战士、高达、变形金刚,我想做一个超级大的机器人,通过这种巨大尺度的冲击力与他们的版图产生关系。我希望大家能够马上在虚拟空间里抬头仰望这个很大的东西。
B:这个机器人的塑造和你《固态诗》里的作品形象有些相似,上面还有印有很多地图。
易承桃:对,其实都是通过一个制图软件做出来的。这个软件的雕塑、制图、笔刷,这些工具会造成很多制作的痕迹。机器人身上的地图是纽约的地图和地铁线路,也是想让它上面有迷彩一样的纹路,某种意义上是另外一种版图。

▲ 《XXX屹立在大地上》,2020,图片来源:易承桃
B:工业设计师的训练以实用性、生产的实体为主,从实体到虚拟,你怎么看待这个转换?
易承桃:对于数字化的生产,无论是感官还是视觉的,我需要更多思考。因为它非常即时、便捷、容易。这是让我很害怕的事情。要生产制作出一件实打实的东西是很难的,但是数字世界中的渲染、呈现,把假的制造成真的一样越来越便捷,这种便捷其实是我持续关注,且持续警惕的,是我现在创作中关注比较多的点。
B:你关注NFT吗?有作品在线上销售吗?
易承桃:我还是不敢完全的跳进去,我也可能不太了解。很多时候别人会质疑我做的是不是艺术,是不是雕塑,是不是绘画,这种事物的延展性会让我兴奋。但是你不可能做出一个NFT,别人说这不是NFT——它终究还是NFT。这一点,我作为艺术家就没那么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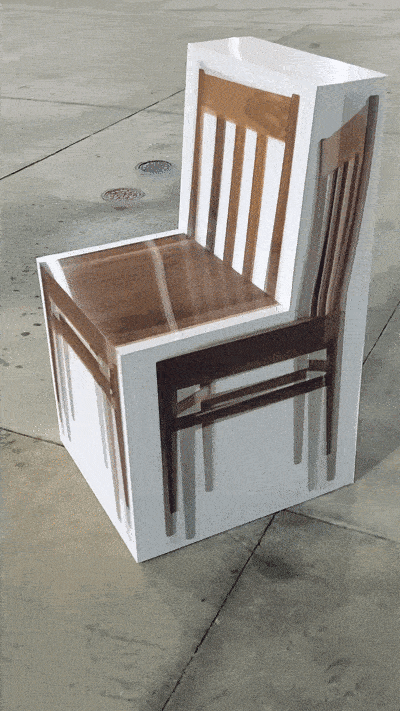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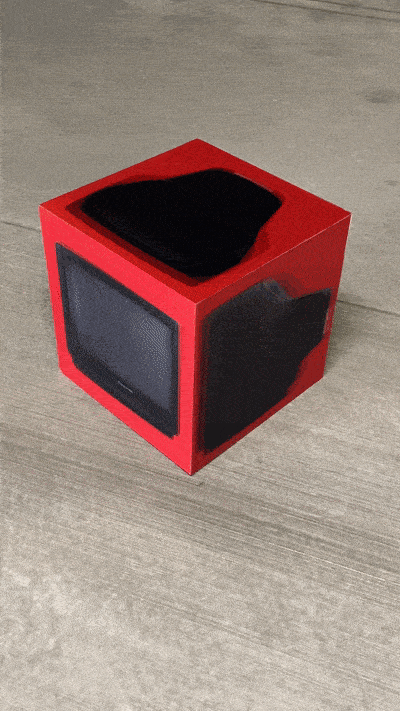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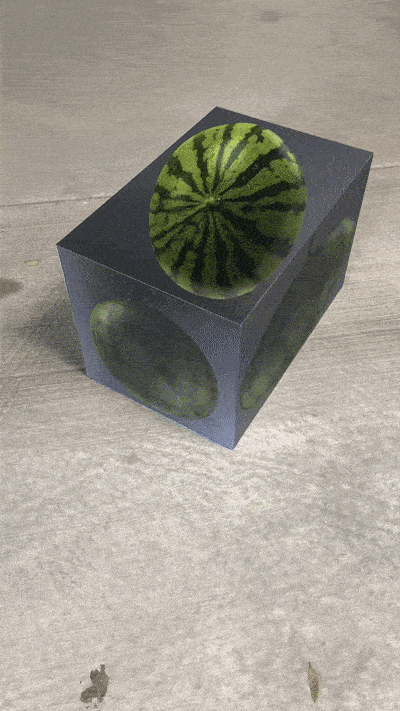
▲ 《Gifs》,光柵印刷,木头,2021,图片来源:易承桃
B:你最近在做的项目“Gifs”,是又回归到实体创作了吗?
易承桃:是的。我之前的很多作品都是数字的,有一种很强的念头想让它物质化,但不是原来的东西。在这种渐进性的思考中,我在想有没有一种表达方式,一只脚踏在现实层面上,一只脚踏在虚拟层面上,两只脚跨着的中间是什么样的姿态和感受,这是我想寻找的。我想迈出这一步,最后迈的是什么样子,用什么材料,具体怎么表达,都是我想研究的。“Gifs”是我对物体性质和图像和本体论思考的一段新篇章,它探讨媒介的限制与可能性,图像与符号的欺骗性。我想我们既然生活中开始充斥这些事物,是不是最该关注的是它们。
B:为什么会选择了椅子、电视机、西瓜这些形象?
易承桃:我将物体分为三大类,椅子是人会坐的,和人产生直接影响的东西。电视是只需要看,用遥控器遥控它,不用去坐也不用去摸。西瓜是要去吃它,最后会消耗掉。后续还有桌子等等,它是托承其他物体的东西。我会把它们分类,一一做出观察和论述。
B:具体用了什么材料,为什么会赋予它动图的呈现方式?
易承桃:作品本身选用了光栅打印的材料。小时候收集很多闪卡,那时候觉得是种奢侈品,有一张闪的、变幻的卡觉得很牛,但现在觉得特别廉价。某种程度上,这种尴尬的材料代表了我们这个尴尬的时代和处境,像是数字的,又是现实物质的,又是塑料的,是动态的,但同时能呈现的变化单调又重复。它像动图——我们这个时代传播力最广的媒介一样,既不是图片和文字,也不是视频,就是来回看它左右闪动的图像和符号,这个阶段我想用它们表现我对现在很多东西的看法。
#03
如何界定商业与艺术的边界
B:参加成都双年展的作品《藏家和他的藏品》,是委托创作吗?为什么想创作这个作品?
易承桃:这幅画是源于比利时画家大卫·特尼尔的作品《莱奥波德·威廉大公的画廊》,一个藏家对于他的藏品非常自豪,展示自己的藏宝阁(Cabinet of Curiosity)。其中还有很多其他和它类似的画,我觉得也可以选择被放在他的画中,成为画中画。
最初创作时有很明显的调侃意味,通过这种图像笑话,一层一层迭进的,博尔赫斯的方式,去阐释图像和艺术在成为财产、被拥有的过程中,逐渐被架空、虚无化的过程。它本质上可能还是一个具有反拥有、反消费色彩的这种东西。

▲ 《藏家和他的藏品》,2020,图片来源:易承桃
B:你也参加过奢侈品牌Bottega Venetta的项目,你的作品大多在挑战消费主义观,怎么界定自己的艺术创作和商业邀约的界限?
易承桃:这还是很单纯的乙方视角的合作。我将它当作是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设计项目,商业邀约本质上是乙方的工作,但是在创作层面上,自己的发言权多了一些,三分甲方,七分乙方的感觉。这次合作感觉全程都获得了支持,没有很多创作层面上的压力,我愿意多交流。如果这中间有对抗,也算是一种接触和见识。创作期间肯定会有很多筛选,最终还是看艺术家和品牌的契合度,如果能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和交流,我不会抗拒。
采写/邵一雪
编辑/舒适波工作室
编辑/舒适波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