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事乐队:致混乱时代里的坏螺丝

新声 NEW VOICE
支持青年人才,为新的梦想共声
由40位伯乐举荐十大创意领域的40位潜力新锐。
由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财新视听、CX创意联合发起的《新声——中国新生代艺术家推新计划》,旨在支持青年人才,为新的梦想共声。
我们邀请来自艺术、设计、电影、建筑、思想、文学出版、舞蹈、戏剧、音乐、美育等领域的专家伯乐,推荐他们最注目的年轻创作者。他们或因奇思妙想、大胆突破而醒目,或有着拔群的锐气、睿智,或凸显出某种当下罕有的质地。他们的成长路径和个性化选择亦可折射时代的特征,他们的先锋、原创、个性,代表了BCAF一贯支持的真实思想表达与多元对话空间的理念。
新锐创作者将获得BCAF及财新传媒各渠道、全网传播的推广合作,也将优先获得国际交流、创作资助、艺术驻留的机会。
第二季10位新锐的深度访谈文章、人物纪录短片自2022年10月28日起,在每周五17:00持续发布。
新声 NEW VOICE第二季第七期 | 荒事乐队

新声伯乐
迷笛音乐节创始人
伯乐推荐语:
2018年在长沙成立的荒事乐队,通过长时长和多元音效的糅合使这支摇滚乐队获得古典音乐所具备的恢弘、诗性的叙事,一种抽象性的回归,其独特的音乐美学和无边界的声音想象力正不断冲击着这个时代日渐空洞的审美同温层。2021年曾作为最值得期待的新生代乐队登上太湖迷笛音乐节的清舞台,同年也获得了迷笛奖“年度最佳乐器演奏”的提名。
张帆
迷笛音乐节创始人
伯乐推荐语:
2018年在长沙成立的荒事乐队,通过长时长和多元音效的糅合使这支摇滚乐队获得古典音乐所具备的恢弘、诗性的叙事,一种抽象性的回归,其独特的音乐美学和无边界的声音想象力正不断冲击着这个时代日渐空洞的审美同温层。2021年曾作为最值得期待的新生代乐队登上太湖迷笛音乐节的清舞台,同年也获得了迷笛奖“年度最佳乐器演奏”的提名。

▲ 新声 NEW VOICE第二季第七期 | 荒事乐队
2018年夏天的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地勤人员理查德偷走一架飞机,说是为了去看一眼远方的虎鲸与它的孩子。临坠落前他在无线电里告诉地面:“我想跟所有关心我的人道歉,他们会为我失望的。我只是一个已经坏掉的人,我猜是不知哪里有几颗螺丝松了吧。以前我没意识到,刚刚才弄明白。”
2020年夏天,中国长沙,5人组成的荒事乐队发布第一张专辑《坏螺丝》,主打歌《太空牛仔》的创作发源自西雅图坠机事件。主唱的迷离女声一遍遍地重复:“我的螺丝松了 我只是一个快要坏掉的人……”
2022年冬天的视频采访,因为疫情隔离,5个人分成了3个对话框,采访是半年来他们第一次见到彼此。回顾《太空牛仔》,一向自我批判的乐队成员谭哲飞破格给出了高评价:“当时理查德说想去看一看海边,其实并不是带着一种悲情或者是赴死的状态,纯粹地在欣赏一种平时见不到的美。(我们的音乐)把平时见不到的美的画面刻画出来了。” 其他成员啧啧赞叹——终于得到了表扬。
这种独一无二的叙事感音乐吸引来了类似审美的乐迷,荒事乐队的经纪人Roy表示乐迷们“高冷”,只是因为音乐的一种彼此追寻与欣赏,不黏着,他们的足迹更多地在播放平台的评论里看到。在网易云,一则《天空牛仔》的评论写道:“也许对于’快要坏掉’的人来说,坠落是一场生命的仪式,通过这个仪式,在欲坠未坠的天旋地转间,以此进入到这个自我解救的太空道场之中。” 或许做这张专辑对于30岁重新组建乐队的成员们本身也是一种自我解救的方式。
谭哲飞是乐队的主创,从高中就开始玩乐队,目前在地方二本院校做作曲老师,被乐队里其他人戏谑为谭教授。他的编曲融入了自己的古典基础。负责人声和贝斯的胡嘉琳(小垂直)算是乐队里表演经验最丰富的,上大学一开始学的是古筝,大三放弃专业改玩吉他,毕业后就以民谣歌手的身份开始全国巡演,现在和谭哲飞一样都在大学里工作。
打鼓的刘炳基是个乡村青年,18岁开始学鼓,现在教打鼓课,拿小时候扛蛇皮袋的劲头扛乐队里100斤的效果器。另一位鼓手肖凡是乐队的财政大臣,疫情夺走了他已从事5年的火锅店采购员工作,现在他也投身音乐教育。何旭聪是乐队里唯一的全职音乐人,在长沙当地开了一个录音棚,被其他成员戏称为“长沙音乐教父”;他爱好文学,喜欢诗歌,贡献了专辑里不少故事感丰富的歌词。
5个各有本职工作的普通人聚了起来,每个人都把自己生活里不那么开心的、阴暗、沮丧和不那么顺利的经历借音乐表达出来,其实做个混沌时代的坏螺丝也没那么坏。

▲ 荒事乐队,图片来源:谜团唱片
快问快答
Q:现在在哪里?生活受疫情影响大么?怎么调节?
何旭聪:我没有太多影响,唯一的就是外地的乐队来不了我这儿(录音)。
小垂直:我在长沙,大学工作上受到的影响不大,教育业应该是受疫情冲击较小的行业了。长沙总的来说封控也不太严重。
炳基:娄底社区之前没有疫情,最近有新冠,所有学校都停课了。
谭哲飞:我生活受的影响会大一些,如果是以往的采访,我会在小垂直的那个账号框里,但现在我跟凡哥在一起。
Q:你觉得当下最亟需改变的人类社会现状是什么?
何旭聪:我觉得是让群体跟群体之间彼此仇恨的那些意识形态吧。
小垂直:对,我觉得是收获信息的不对等所导致的意识形态的差别,搞得现在大家都很对立。
谭哲飞:每个人都困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不了解,不信任,不作为。
Q:你从事的职业能够有助改变这个现状吗?
何旭聪:有那么一丢丢吧。其实音乐是一个展现的东西,你能够去说一些故事,说一些事情,表达一些情绪,帮助大家彼此之间不那么仇恨吧。
谭哲飞:我倒觉得可能不是仇恨,就是不了解,不信任。大家只与自己的小圈子交流,圈子外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根本就不知道。
何旭聪:你这是在说阶层。
谭哲飞:我都不想说阶层这个概念,因为按道理说我们都是无产阶级。我做老师,本来以为是可以改变现状,但阻力比我想象的大。
Q:你最想改变的个人现状是什么?
何旭聪:我就希望自己的拖延症稍微好一点。
小垂直:你放屁吧。我没有什么特别急需改变的现状,希望自己变得更厉害吧,做饭更厉害,弹琴更厉害,没有什么特别不满意的现状。
谭哲飞:我想自己自律一点,尽早能从这个三观不合的地方跳出来。
炳基:我希望自己水平更好一点,懂得更多一点。
肖凡:一能多挣点钱。二为新专辑做准备。
Q: 你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小垂直:很重要的来源是朋友圈,很多实时的消息比你看新闻可能会更快一些。
炳基:那是信息茧房。我关注最快的方式是我们各大领导直接发的通知。我在娄底从事培训工作,说关门就关门了。
谭哲飞:时事信息大部分还是互联网,但是我会尽量多地从不同的平台上面找。现在不同的平台使用人群确实特别不一,回答风格也都不一样。如果说系统的认知来源,基本上还是看书比较好。
何旭聪:我基本上也就是朋友圈,偶尔会去YouTube找一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看。
Q: 你的童年震撼和缺憾是什么?
谭哲飞:当年我的钢琴老师给了我一耳光,让我彻底放弃了弹琴几年,我再也不想去上课了。如果小时候练得更勤快一点的话,对现在更有帮助。
炳基:你再还他一个耳光。
何旭聪:我姐姐跟我讲整个大自然的循环系统,就是水是怎么蒸发到天上变成雨,树是怎么长出来的,我觉得挺震撼的。
小垂直:我的童年还挺野的,基本上是在户外度过。非要说有什么缺憾,我跟老谭在一起之后接触了武侠小说和优质的动漫,觉得可能小时候都在外面傻玩,真正好好看书或者是看电视的时间并不是很多,这个还是有点缺憾。
炳基:我小时候最震撼的是我总搞不清楚读书是为了什么。
肖凡:他(炳基)小时候要挑西瓜的,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所以到现在为止,炳基也是我们当中最能干活的人。
炳基:我为我自己的无知而震撼,小时候蛇皮袋子能挑一百多斤,我怕爷爷奶奶挑多了,经常一个人扛。
肖凡:我最震撼的一次演出应该就是炳基直接双手抬起来重达一百多斤的效果器,双手抬起来越过安检的栏杆,当时震撼到我了。
Q: 你第一次挣钱是做什么事?
何旭聪: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在一个垃圾堆里挖到了几枚民国时候的货币卖,挣了百十来块钱。
肖凡:你是怎么知道那个地方有银元?
何旭聪:我有喜欢到处乱看的毛病。
小垂直:我很小的时候在军区院子里,夏天快过完的时候,树皮上面会粘着很多蝉蜕,我们就收集下来卖给旁边的药店了。人家本来不收这个东西,只是觉得我们是小朋友辛苦,给了我们一点钱。
谭哲飞:我这算半诈骗。高中就我们几个弹琴的,说开培训班。同学找他们的爸妈要钱,我们对半分,象征性地上两节课。其实根本没搞什么培训,就是把家长付的学费与同学对半分。
肖凡:小时候每天会经过一个铁路,无意中发现上面会掉下一些碎钱下来,于是每天放学沿着铁路走,一个月也有不少收获。
Q: 现在的职业有多大程度是谋生?如不必考虑生存,你的创作/工作会与现在有何不同?
炳基:我是靠这活儿谋生的。
肖凡:我现在和他也一样了,做采购的5年火锅店今年因为疫情倒闭了,自己弄了一个工作室,教一些小朋友。
谭哲飞:我现在教书也算是谋生,很多人觉得我适合当老师,但我没有那种奉献精神,我有职业精神,回去把课上好就可以了。我从事助教六七年了,没搞过职称,因为我不会搞那些东西。
小垂直:对我来说现在的工作就是谋生。如果不考虑生存,我最理想的生活是每种工作都尝试一下,喜欢的我就多做一下,不喜欢的就不干了,我想尝试不同的人生。
Q: 你睡前刷多久手机?有被某种意识裹挟的时候吗?
炳基:每天都会被裹挟到凌晨三四点。我就算用手机翻页,也可以一直翻四小时,最近疫情白天没事儿干,不用上班,我就彻底懵了。
谭哲飞:我刷一个小时肯定睡着,我会去各大平台看同一个事情不同人的观点。
肖凡:我只看我想看的观点。
小垂直:为什么现在意识形态对立得这么严重,我觉得大家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部分。
谭哲飞:所以才要去看别人的观点。有时候我挺喜欢看他们吵的,互相扣帽子。
Q: 去年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谭哲飞:相比今年来说,去年什么都高兴。
小垂直:我已经不能很清晰地回忆起去年发生了什么,感觉这三年的生活还蛮程式化的。
何旭聪:最高兴的就是巡演了。
小垂直:对,巡演出去又紧张又放松的状态是最高兴的。今年我觉得精神生活一片空虚,没有演出看,没有什么朋友的聚会,我们一个乐队都大半年没聚了。
Q: 作为艺术家,你最看重的三个品质是什么?
何旭聪:真诚。
小垂直:(你的答案)跟我一样。忠于自我表达,不敷衍观众。
谭哲飞:真诚,太多的东西是营销出来的。
炳基:最重要的是不一样,有个性,但不是不好交流的那种。
#01
叙事性的音乐

▲ 电影《荒蛮故事》,图片来源:豆瓣电影
B: 乐队名字来自阿根廷电影《荒蛮故事》,小人物如何以眼还眼的6个黑色幽默故事,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个故事?
谭哲飞:我个人比较喜欢两个故事:一个是在公路上面两个人斗气开车,最后就同归于尽炸死的那个。我觉得那个跟生活比较近,因为我有时候脑子里面幻想过要干这个事。另外就是最后疯狂的婚礼。
小垂直:我最喜欢的是炸交通局的故事,我觉得是每个人内心里面真实的投影,应该都会想去做这个事情。
何旭聪:我最喜欢开车的那个,和自己挺像的,因为它够野蛮,只是被所谓的文明给教化了。
B: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荒事乐队在中国年轻一代摇滚乐队中的独特性么?
谭哲飞:我个人先诚实地回答,没有任何先锋性,虽然相比大家听到的常规歌曲,我们确实有些不一样的结构或者调性,但是这些东西二十世纪初别人就玩过了,我怎么好意思评价成先锋性。我觉得在结构和表达形式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像乐队式的戏剧张力,不是一首抒情的歌曲。我会想把元素音乐的东西搬到通俗音乐上,这比较独特。
何旭聪:我不知道古典音乐现在最先锋的是在做什么,这个可能教授更清楚一些,在通俗音乐范畴里面会比较有一点听觉门槛而已。
B: 时隔两年,怎么评价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谭哲飞:2020年发过专辑之后,我除了排练演出,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是因为疲倦,另外就是我很容易否定之前的东西。我上个月才第一次打开流媒体,认认真真地把《太空牛仔》听了一遍,觉得我们还挺厉害的。无论从情感、画面上都非常到位,情绪的递进、画面的切换、连贯性、音色、旋律、我觉得都挺好,这个气质就是跟别的音乐不一样。
小垂直:真难得啊,他从来没有表扬过自己,一般都是否定自己,觉得是垃圾。
何旭聪:对,总觉得我们做的音乐没被大家认可。
谭哲飞:他们认不认可跟我们没关系。《太空牛仔》确实很好的,当然,何旭聪一直怪我他前面的人声给他处理得不好,我觉得挺好的。好的第一点在于它跟别的音乐特别不一样,运用了很多二十世纪古典音乐的一些无调性,包括一些调性的游离,完全没有调性的处理,营造出的一种紧张感。不是靠简单的音色营造,真的靠音乐语言营造出来的,然后一步一步过渡,其实那个画面感是真的非常强,包括中间进入一段弦乐之后,整个音乐变得舒缓开始,就是何旭聪和小垂直两个人合唱的那一段。我觉得音乐上的情感包括歌词我也挺喜欢的。
有些人不理解那些歌词在讲什么,我觉得其实写挺好的。何旭聪改了那一句歌词“鲸鱼盛开在彼岸”,因为《太空牛仔》这个故事是把两个新闻串在一起的,当时还有个鲸鱼妈妈一直托举着死去的宝宝的新闻。最后是一段纯器乐,那个氛围真是刻画得很到位。
当时理查德在驾驶的过程也说了,想去看一看海边。其实并不是带着一种悲情或者是赴死的状态,真的是纯粹地在欣赏一种平时见不到的美,我把那种他平时见不到的美的画面刻画出来了。

▲ 鼓手肖凡,图片来源:谜团唱片

▲ 鼓手刘炳基,图片来源:谜团唱片
B: 双鼓配置最难的点在哪里?
炳基:打得整齐,这个实际上比我想象的难。我们两个节奏、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只是需要在同一个表达的情绪里,能不打架其实挺不容易的。比如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自己是那种想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的打法,很死板,跟凡哥的鼓有的时候会不在一个频道。
谭哲飞:他们两个的配合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创作。对于一个电声乐队来说,鼓的律动部分是很重要的,他们能默契到什么程度对我们的配置会有很大的影响。
#02
灵感来源

▲ 乐队主唱小垂直,图片来源:谜团唱片
B:与“坏螺丝”的来源相比,有没有过被身边新闻触动到类似的程度想要创作?
谭哲飞:我那天和从事电影行业的朋友聊了一下,我可能下一张(专辑)还是有歌词,说实话到下下张的时候,我不想有歌词。不是说歌词不好,而是我很讨厌自我审查的过程。自我审查真的很痛苦,我们甚至还要开会来想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怎么措辞这个事情,这就像被阉割一样,特别难受,还不如不写。
B:西雅图机场的新闻,也启发了其他三个乐队的创作,话梅鹿《Insufficient Postage》, Fayzz《他偷走了西雅图的天空》,凹与山《查理》,有听过么?觉得如何?
谭哲飞:我就听过《查理》,其他的我都没有听过。当时有人说我们这个跟《查理》比起来太过具像。其实我想说大部分我们听到的歌,严格来划分的话,它是属于抒情类歌曲,通过一个旋律和歌词来表达某种情感。为什么不可以做一种叙事性的音乐,或者通过音乐讲故事,构建场景?我们平时都是习惯从视觉上去看画面,音乐也可以营造画面,可以营造一个画面情节,甚至可以离开歌词去做这个事情。你能用一个这么抽象的东西来做一个很具像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很不得了的。

▲ 乐队主创谭哲飞,图片来源:谜团唱片
B:想问问谭哲飞,大学教学的经历有反向刺激了你的创作吗?带来了什么灵感?
谭哲飞:基本上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彼此不重合。我会观察我的学生,他们和我当年读大学有什么不一样,和大城市的学生怎么不一样,比如在开阔性上。我会试着去观察他认知上的东西,这是我一些灵感的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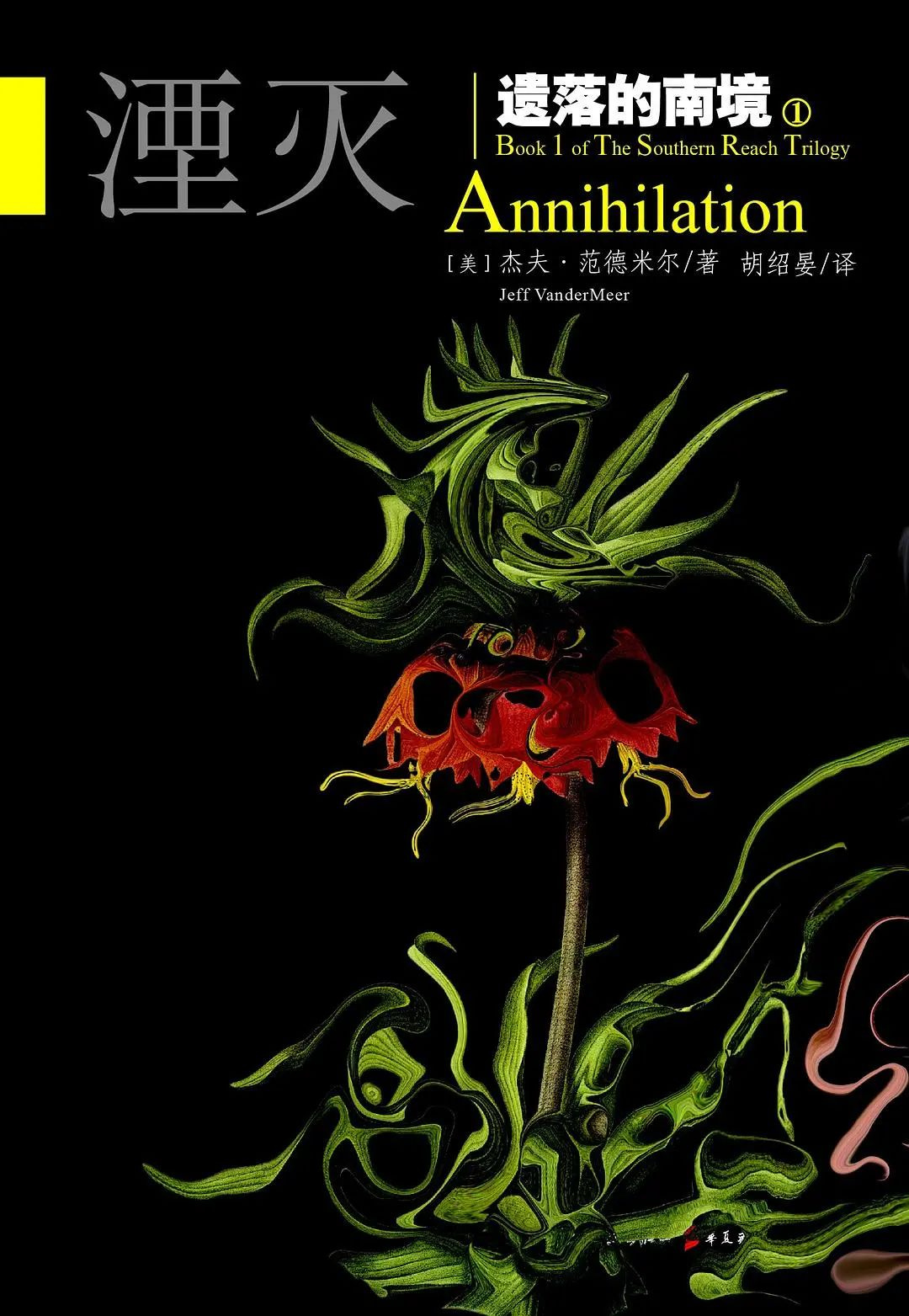
▲ 受美国作家杰夫.范德米尔创作的新怪谈三部曲之一《遗落的南境》的启发,何旭聪创作了同名歌曲的歌词,图片来源:豆瓣读书
B:何旭聪平时会看什么科幻小说?
何旭聪:偏硬科幻的吧,最近看了一个俄罗斯作家谢尔盖·卢基扬年科的《星星是冰冷的玩具》,他还在里面把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给复活了,我觉得挺浪费的,毛子民族的浪漫。以前挺喜欢像海因莱因的、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这些比较经典的。他们那一代作家有一个特质,就是站在一个文明的角度上去书写一些东西,探讨文明最终去到哪儿,很少描绘一些特别小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科幻迷,特别不喜欢看《星球大战》,它其实在讲的还是一个文明架构上面的权力之间的争夺,是太空版权力的游戏。《2001:太空漫游》一共是四部曲,一直到2061太空漫游,整个是交代一个文明的位置和脉络,极富想象力,包括很多近地轨道的外星城,在土星上人类的基地,大胆地想象土星的星河。他都不是瞎想的,他知道土星表面的元素是什么,有多大的压力,真的很有可能是一个钻石。
因为人造卫星的近地轨道是克拉克在阳台上想出来的,NASA现在每年还会象征性地给他一块钱版税。之前他好像是一个技术兵,为了写小说做雷达。他会通过写作去预言,想象科技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科技成了这个样子之后,我们的政治经济格局再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把它变成故事,这种东西可能更吸引我一点。
#03
被更惺惺相惜的人看到

▲ 重庆巡演给了乐队很大的信心,图片来源:谜团唱片
B:你们的粉丝是什么样的?平时怎样跟粉丝互动?
谭哲飞:从我对他们浅显的了解来看,他们都钻研过的我们的音乐,觉得你作品好就是好,觉得你作品不好,就不会跟你多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们也有微信群,基本不聊。首先我们这一年是歇着的。另外——我也不喜欢称他们为粉丝,叫乐迷群——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高冷。他们不留言,他们跟我们很像,我们也跟他们很像,我们也不留言。
B: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的巡演经历或者现场互动吗?
谭哲飞:2020年,在我们决定巡演出发的前两天我外婆去世了,我们算了时间,我得给我外婆守灵三天,乐队里他们三个人先过去了,我和垂姐两个人最后面奉上香之后就立马赶飞机。飞机误点,到达场地离开演只有一个小时了,加上我那几天状态特别不好,所以在第一场成都,我一直没有从那个状态中间走过来。第二天我们在重庆,大概就50来个观众,但是第一次给了我们信心,基本上只要给鼓点,下面人就嗨了,就给你非常强的反馈,所以那天感觉特别感动。
B:你们希望一直保持这种不以音乐谋生,靠正职收入保证生计的方式创作演出下去,还是也希望能够单纯靠音乐自给自足?后一种情况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谭哲飞:不能说不以音乐谋生,我干活也是在做音乐,何旭聪也是帮别人做专辑录音,我觉得都OK。只能说不以乐队谋生。我们当然希望就靠演出就能挣很多钱,但这个特别特别难。现在这样也有一个优势,创作的过程中我可以不去考虑市场化,不用指着它去挣钱,可以想怎么写怎么写。
B:你们现在看到身边的乐队是什么样的?都不是靠这个自足?
小垂直:纯靠乐队赚钱的,基本上都是富二代。

▲ 广州巡演的观众们,图片来源:谜团唱片
B:小众音乐怎样找到线下巡演市场,巡演城市是怎样定的,是演出运营者找你们还是反之,演出报酬目前是什么行情,切身体会到的演出市场变化是怎样的?
Roy:其实和主流艺人一样,首先有作品,根据作品找对应的客群。我们(公司)提供的主要服务还是让乐队和市场去连接,让听众听到他们的歌。我们本身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厂牌,只把一个门类做好,比如我是卖包子的,我就只把包子卖好了。我们签的艺人比较垂直,听众喜欢听这一类的,他的耳朵就会喜欢这类的音色与艺术表达。
我们也会去看后台数据,广深后台数据比较好,就会去定这个城市,像数据上面没有南宁,或者海口,但是第二轮巡演的时候,作为一个宣传的作用,还是会去的。一般刚开始先在大城市发酵,有了口碑以后开始上一些音乐节。荒事乐队没有上过综艺,推起来就比较慢。荒事乐队其实是为理想主义者发声,不少圈里的人愿意支持这类小众的音乐。注意,小众不是贬义词,只是针对它市场的客群数量来说。
专辑收入来源,实体方面有头版黑胶,一共200张,在第一轮巡演的时候就已经全部售罄了。CD的销量也不错。乐队的钱没办法保证一个运营人员的开销,平台发布本身不赚钱,我们对抗着不公平的流量算法,实际的收益可能是百分比小数点后几位。一个乐队只要在垂直领域被认可就很不容易了。
B:和法国的音乐人Elbi合作是什么样的?
谭哲飞:那个歌是一个混合产物,她出一个节奏动机,我们就拿这个动机写点什么,器乐构建出来,她来构建一点旋律,就这样子来回碰撞写的,不是应付。作品现在听不太行,但我不知道两年后能怎么回答你。
B:对乐队来说迷笛提名“年度最佳乐器演奏”意味着什么?
谭哲飞:最佳歌曲或者新人什么之类的很正常,乐器这个感觉不太能担得起,但是我觉得是个好的鼓励。而且对于这俩鼓手开培训班来说挺有用的,你看这还挂着最佳提名的那个东西,可以骗学生的。
肖凡:其实也没有,人家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提,小城市基本上不大了解。
B:未来想跟什么样的其他音乐人/艺术家做跨界合作?
何旭聪:美术家。
谭哲飞:可以和一些装置艺术实时的这种音乐现场结合在一块,或者是用戏剧的形式一块来做一个舞台呈现。
何旭聪:跟打太极拳的老师父一起。
采写/郑若楠
编辑/舒适波工作室
编辑/舒适波工作室